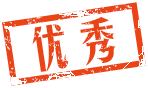|
搬到新大楼时恰逢栀子花开,上班的第一天,我就绕着大楼北面规划整齐的绿地,想找一棵栀子花,但寻遍围墙内每一个角落,只有满院桂树,还是宿舍的小院好,面积虽不大,但春有玉兰、迎春,夏有月季、火红的石榴花、蜀葵和洁白的栀子,秋有桂花冬有腊梅,四季花常开。 还好,大楼南面有一片空闲的土地,周边被附近勤劳的老人种上了蔬菜、瓜果,成了菜园,腹地因不方便耕种,依旧荒芜着,任野草疯长、野花恣意绽放、芦苇从生,有蜂蝶乱飞、昆虫浅吟,甚至还有只野鸡,时时“咕咕”的呼朋引伴,可惜它的家园已被钢筋水泥深度包围,这只不知为何陷入其中的野鸡出不去,别的同类也进不来,我只能无能为力地看它孤零零的站在荒草中间,听它日复一日空洞无助的叫唤。 很喜欢眼前这块任自然万物随性生长的空地,闲暇时就站在三楼平台上,看菜园里老人翻耕出的土地,有的黑黝黝的肥得冒油,有的却白得发硬、贫瘠干瘦。懂得养护土地的人,地越种越肥;一味的榨取、掠夺的人,地只能越种越瘦。想起生命里人来人往,有人久处无厌、甚至愈久弥坚,有些人乍交之欢后,渐渐就淡了散了;看空地里蜿蜒延伸的小路,记得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我相信,空地里那些弯弯曲曲的灰白土路,是辛勤耕种老人们踩出来的。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城市中一条条见山劈洞、遇河架桥,横行直撞的笔直公路,他还会固执认定: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是以摧毁沿路的房屋、侵占农田、砍伐古树、撕裂大山为代价,再用水泥沥青浇灌出来的?再次注视眼前绕来绕去的羊肠小路,徒然感叹,世界变得真快! 骨子里就喜欢那些自然天成、野逸灵动的一切,本能的排斥和抵触人类以万物灵长自居,按自己的意愿、喜好,随心所欲地摆布周围的一切。每次看到养护工顶着烈日拔除草坪上野草时,就十二分不明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借用肖恩·格雷塞尔的话:它们属于这片土地,它们有权利呆在这里。人类非要厚此薄彼,拔掉这些这些不需任何养护、自然生长、可以随意打滚、踩踏的草地,却自以为是地种那些需呵护备至,离不开化肥、农药、除草剂的滋养,得到的是蝴蝶、蜜蜂等昆虫不愿驻足,人类只许远观不能亲近被严重污染的绿地。 史铁生说地坛是上帝苦心安排给他的一个宁静去处,遥远的地方我不清楚,就我生活的小城,那片我曾常去散步的栀子林、门前拐弯处荒草肆意生长的土坡,应该都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但短短几年,全部被钢筋、混凝土、水泥一点点蚕食殆尽。我知道,不久的将来,这块空地也会毫无悬念地被丈量、被规划、被篡改成千篇一律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包围圈内仅存的一点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将再次遭到无情的挤压、成为日益扩张城市的一部分。需要改变的是我,从来就不应该是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