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22955
- 积分
- 708
- 威望
- 1418
- 桐币
- 849
- 激情
- -1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197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7-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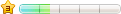
桐网贡生
 
- 积分
- 708
 鲜花( 0)  鸡蛋( 0)
|

楼主 |
发表于 2009-3-26 08:54:47
|
显示全部楼层
至于方苞、姚鼐的故居,也不知何处。此刻的桐城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县级市。商业街上的一家接一家的店铺、中心广场丑陋的不锈钢雕、河畔的巨幅地产广告牌,只有那座仍旧素雅、端庄的文庙,稍微流露着这里的与众不同。在十七、十八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桐城学派制定了文章写作的标志,塑造了十几代人的思考方式,方苞、刘大櫆、姚鼐是其中最著名的三位。在某种程度上,桐城对于中国,就像十九世纪的新英格兰之于北美,才俊集体性的涌现,交相辉映。, e1 j' a, K) e, t. c+ F% F
7 L& L8 _2 L7 f( y, x但是新英格兰的爱默生、洛威尔、梭罗,倡导的是个人主义精神,是自由的想象力,是对于政权的不合作。但桐城的学人们面对的则是一个强大得密不透风的政治权力。他们兴起的年代,也正是文字狱肆虐的年代。放弃对政治、社会的整体和深入的思考,学者们躲入考据和形式主义的小世界。你可以称赞他们开辟了更为精致的研究方式,一些乐观主义者甚至从中预见到了科学方法的兴起。但是回避了价值判断,却也使所有的钻研变得琐碎。9 r3 a' S0 q' S. B% U/ R8 \
7 {3 v) i. s: q+ K0 Y5 V0 G+ l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或许也间接的解释了在昌盛的、纵横全球的十八世纪后,中国为何一头扎入了失败的连环陷阱。中国丧失了内部辩论和自我批判、反省的能力,对于陌生的挑战反应迟缓,一个错误重叠着另一个错误,最终系统性的崩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