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9485
- 积分
- 1910
- 威望
- 207019
- 桐币
- 0
- 激情
- -26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0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4-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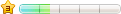
桐网贡生
 
- 积分
- 1910
 鲜花( 0)  鸡蛋( 0)
|
皖文化刍议
方国根 罗本琦
〔摘要〕“皖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有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有他的影响和贡献,因而应有一定地位,如同齐鲁文化、秦晋文化等一样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皖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即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和间断性、历史继承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而造成皖文化这些特点的原因在于安徽地区的经济、地理和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使皖文化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的安徽学子。
〔关键词〕皖文化;历史发展;特点;成因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01)01-0125-06
安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安徽人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生息,在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留下了不朽的精神遗产。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江淮大地上人才辈出,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们活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舞台上,或以文治武功流芳千古,或以学术思想形成重要学派,或以诗文蜚声文苑,或以丹青驰誉艺林,或在科学技术园地大放异彩,对中国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有些皖籍学人长期流寓外地,也有不少外地学子客居皖境。但他们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都有着共同的历史界域或渊源,即都根植于安徽这片热土,并在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局部区域形成共同的或者近似的学术风格,从而汇聚成一个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区域学术文化体系。我们姑且把由这些杰出人物创造的,有着共同的历史界域、渊源及近似风格的学术文化称之为“皖文化”,或称之为“安徽文化”。诚然,就中国古代地域文化而言,“皖文化”没有像齐鲁文化、秦晋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那样已明显形成既相对独立又内在统一的地域文化圈,特别是在历史沿革中,受地理环境及政治等因素的限制,皖文化经历了由北向南的发展,皖北、皖中、皖南之间的人文学术传统存在着差异,但是,就某时期的皖境学术中心而言,如春秋战国时期皖北的老庄学派、三国时期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的“建安文学”、明清时期的徽州经学和桐城文派,他们在学术宗旨和研究方法上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皖文化中的桐城文化、徽州文化及两淮文化给予较多的关注,却对皖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则未引起重视。本文试图用“皖文化”概念来界定或涵括安徽历史沿革中所形成的这一区域学术文化体系,并着重对皖文化的历史发展、特点及其生成原因做点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皖文化的历史发展
皖文化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1980年,和县龙潭洞猿人头骨化石与巢县银雀山村猿人枕骨化石的发现,表明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江淮地区就有了人类的活动。而1998年10月—11月,在繁昌癞痢山人字洞喜获旧石器考古大发现,出土200万年前石制品和骨制品化石,经有关专家确认,系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人类文化遗物〔1〕;又在含山县铜闸西南的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发现大型祭坛、祭坑,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1000多件,玉器种类繁多,刻划精美,极为罕见,特别是呈螺丝状的石质钻头,为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首次发现〔2〕。至于新石器时代,氏族群体已经遍布安徽全境。解放初就已发现新石器遗址一百多处,分布区域北至萧县花家寺,东至嘉山泊岗和灵璧蒋庙村,南至绩溪胡家村,西至临泉老丘堆〔3〕。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安徽发现古文化遗址三百多处,其中多数属新石器时代遗址〔4〕。大批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不仅表明当时的渔猎业、饲养业和农业都比较发达,而且在出土文物中,石器的磨光、穿孔,角器的磨琢,陶器上的饰纹,也表现出较高的工艺美术水平〔5〕。尤其是陶器上的花纹,种类繁多,说明当时的人们有着爱好美术的情趣,并有余力从事工艺美术活动。当中原氏族进入阶级社会时,遍布安徽的氏族群众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或近似于国家的氏族组织。商代泗县北部的徐国就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西周时期的江淮诸部落也具有了国家的雏型,并创造了更高级的文化。1959年,屯溪发现两座西周古墓,出土文物中瓷器的完整性、系统性及工艺水平,都是中原及周边地区罕见的〔7〕。从大量民间传说中,我们也能窥视出安徽原始文化的概貌。古冶子铸剑庐江冶父山、干将莫邪铸剑芜湖赤褐山的传说,反映了早期安徽人民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关于禹的传说则将两淮民歌的口头创作时期推到原始社会末期。相传夏禹治水经过涂山(怀远县境内),并与涂山氏之女相爱,禹匆匆离别后,涂山氏之女作《候人兮漪》表达思念之情。淮河民歌至西周时已经十分流行,并传入中原,登上大雅之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冠十五国风之首的《周南》、《召南》相传为周、召二公征“淮夷”时,采撷淮河民歌修饰而成,《小雅·钟鼓》中所描绘的也多是淮河风光。
但学术文化是在文学产生以后,随着专业学术研究者的诞生而形成的。皖文化产生的历史条件至春秋战国时期方成熟,管子思想、道家学派以及楚辞的产生,标志着皖文化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奠定了这一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在诸侯争战中崩溃。社会激剧变动引起思想意识上的巨大变化,人们的世界观以及对事物的认识呈多元化发展,从而产生了众多的学术流派和一大批专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另一方面,大大小小的统治集团为了在激烈的争夺战中获胜,也积极拉笼人才,各派学者得以寄居“高门大屋”,畅所欲言,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形成了百家争鸣、私家著述的风气。安徽地区至春秋时已经是分国林立,曾有徐、楚、吴、越、蓼、六、皖、巢等诸侯国,并成为诸侯争霸的主要战场之一,不论晋楚争霸,还是吴楚争雄,江淮地区都是争夺的目标或必经之地。公元前632年,楚国问鼎中原受挫后,迅速转而向东,将两淮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584年开始的吴楚争夺战,持续170多年,主要战场都在安徽境内。长期的战争给江淮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孕育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管子思想和老庄道家学派,同时,随着楚辞文学的产生,两淮民歌也由口头创作发展到书面创作,文学形式也发生变化。
秦汉以后,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安徽传统文化也进一步融合到更大范围的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体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皖文化的发展与华夏文化的兴衰休戚相关,并受到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制约。但同时也保留着自己的风格、传统,有其自己的发展轨迹。
秦王朝建立以后,采取钳制思想、摧残文化的高压政策,因而在其短暂的几十年中,学术文化没有什么进步。皖文化也不例外。
西汉初年,统治者在恢复经济的同时,也“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又除“诽谤妖言”之罪,客观上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皖文化也在继承道家思想和楚辞传统的基础上,获得较大的发展,纵然在“独尊儒术”的时代,也产生了以贬斥儒法、崇尚老庄为宗旨的学术名著《淮南子》。东汉时期,谶纬之学成为官方哲学,但反谶纬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皖文化当然不能不受这种思想斗争的影响。因而在皖籍学人中,既有正统知识分子的代表(如桓荣),更有反谶纬神秘主义哲学的进步思想家桓谭、范滂等,正是在这场斗争中,产生了中国早期唯物主义的光辉著作《新论》。安徽学人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也是巨大的,东汉末年以庐江地区为背景的《孔雀东南飞》代表着这一时期安徽文学艺术的水平。
东汉末年,社会发生巨大变动,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均不同程度地得到继承和发展,并呈自由解放的趋势。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及其领导的建安文学,并造就了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的时代风格。魏正始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建安学人积极进取的精神,被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老庄思想因而深入到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皖文化受老庄思想影响尤其突出。这主要是因为,道家学派本来就是在先秦江淮地区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秦汉以后又在皖文化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从嵇康身上,我们不难看到老庄思想对魏晋时期皖籍学人的影响。他一方面尚奇任侠、疾恶如仇,“非名教,薄周孔”;另一方面又追求恬静寡欲,好服食,求长生,他的诗文也着重表现清逸脱俗的境界〔8〕。安徽绘画艺术至魏晋时期才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也与这一时期的政治背景与老庄思想深入人心分不开。汉末以后,由于战争频繁,统治者无暇顾及对艺术的管制,绘画艺术得以摆脱官府的垄断,不再是纯粹的宫庭贵族装饰的工具;同时,由于两晋南北朝时佛道盛行,大批佛院道观的兴建也为艺术人提供了绘制佛道壁画与佛道仪像的机会,从而不仅开拓了绘画艺术的新领域,而且绘画艺术的风格也发生变化。尤其是东晋王朝建立后,画家多受南方地理风情及道家思想之熏陶,我国绘画艺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产生了自由艺术之萌芽。〔9〕
经过近四百年的社会大动乱,至公元589年,终于实现国家的统一,在此后的数百年的时期里,隋唐统治者除在经济方面采取积极发展策略外,在用人制度上也实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对宗教文化则采取三教并立,兼容儒、释、道的方针。这些措施客观上为隋唐学术文化的繁荣开辟了道路,但与周边文化相比,这一时期皖文化的发展是有限的,除张籍、李绅、杜荀鹤等为数不多的诗人在文学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之外,在学术思想、科学技术以及绘画艺术诸方面则没有引人注目的建树。
宋代在政治、军事上都十分腐败和暗弱。然而,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以及学校教育的发达与刻书业的繁荣,封建学术文化却获得了全面发展。皖文化也扫除了隋唐以来冷冷清清的局面,南宋期间,安徽一地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在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此外,黟县汪纲开考古学之先河,由图经发展而来的地方志的创作也十分兴盛。值得引人注意的是,自南宋开始,皖文化发展的区域结构已发生实质性变化,皖南地区尤其是皖南徽州成为安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公元1275年,元军占领大江南北,安徽全境沦入元统治者铁蹄之下。在元帝国统治期间,我国学术文化实际上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元代学术思想以理学唯心主义为正统,然而,就当时所谓造诣最大的大儒许衡而言,也缺少学术建树,多为拾宋儒之牙慧。在文学艺术方面,也仅杂剧发展较快。皖文化当然不可能有所进步。
明代早期,朱氏王朝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使得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经历了元末战争破坏之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在文化思想方面则受到严厉的控制,程朱理学成为钦定的唯一合法的学说,在用人制度上实行严格的形式主义的八股取士制度,并对封建文人采取笼络与镇压并重的手段。因而,明代前期的学术文化比较暗淡,皖文化亦未能从元代低谷中走出来。至明中叶,随着心学的崛起,理学思想的绝对权威和一统天下的地位发生动摇,学术界沉闷的空气才有所缓解。但皖文化的再次兴盛,还是明末清初的事。明末清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从而再一次唤起安徽学人的爱国主义传统,经世致用成为一代学人的治学宗旨。桐城学者的早期代表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等,不仅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载入史册,更以其坚贞的民族气节与务实之学风为后人称道。融民族精神于学术研究,是这一时期皖文化的特点,也是皖文化再次走向繁荣的动力。清代文字狱迭起,至乾嘉期间,统治者进一步强化对文化的高压政策,仅乾隆六年(1741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间,就有文字狱63起,每年都有文字狱发生,杀人焚书成为平常的事〔10〕。安徽地区亦先后发生戴名世《南山集》之狱、孙麻山之狱与和州戴移孝之狱等多起文字狱的惨剧。在清王朝高压政策之下,学人禁若寒蝉,埋学于故纸堆里讨生活,考据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而显得异常兴盛。另一方面,清王朝统治者用以笼络文人的手段也超过前代。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再开“博学宏词科”,被举者竟有276人。〔11〕笼络政策诱导了大批封建文人为功名富贵而致力于学术研究。徽州经学、桐城古文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并获得迅速的发展,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明中期以后,安徽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皖南手工业和商业突飞猛进,安徽学人在科学技术以及绘画、声乐、戏剧等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将皖文化推向历史上最高峰。
安徽进入近代后,桐城文派、皖南徽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遗风犹存。在鸦片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安徽境域更是群星灿烂,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人志士,既有洋务运动的先锋李鸿章,又有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胡适与陈独秀,他们在继承皖文化传统的同时,也为皖文化注入近代文明的精华,将皖文化推向一个新的时期。
二、皖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
皖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如下主要特点:
首先,皖文化发展的曲折性和间断性。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长河中,皖文化虽只是一支涓涓细流,但它却源远流长,且其发展过程曲折,具有明显的间断性。在春秋战国以降的数千年历史中,皖文化几度兴衰,差不多呈波浪式发展。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皖文化在继承先秦安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然而在隋唐五代的近400年间,虽然安徽地区亦不乏杰出人才与成就,但较诸前代已显得十分冷清,与同代周边文化相比,也有很大差距,直至北宋王朝建立以后,才开始扫除隋唐时期寂寞冷清的局面。在两宋时期,安徽虽然长期烽火不断,但在学术文化方面却有突出的成就。公元1275年,贾似道兵败芜湖,安徽全境落入元军之手。在此后的100多年里,皖文化基本上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至明中叶以后,才迎来皖文化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其次,皖文化发展的历史继承性。皖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思想与楚辞传统,对秦汉以后的皖文化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是贯穿于皖文化发展过程的主线。在学术思想上,从道家学派到汉初的黄老之学,再到魏晋玄学,一脉相承。北宋初年,陈抟开两宋客观唯心主义之先河,由于陈抟生于老子的故乡,其学术思想深受老庄影响,因而经过隋唐数百年的间断,陈抟对道家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两宋理学唯心主义体系实质上是儒、释、道学说的交融与糅合。在文学方面,从汉乐府诗歌至建安文学,也是与楚辞一脉相承。唐代的张籍、李绅、杜荀鹤,宋代的梅尧臣、张孝祥,无不是现实主义作家中的典范。至于《儒林外史》,更是封建末世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道家思想与楚辞现实主义传统,也是安徽艺术发展的主旋律。晋代安徽画坛的繁荣,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老庄思想的影响,两晋著名画家的力作大多成于我国文化中心转移到深受老庄思想浸淫之地的长江流域之后。在绘画风格上,从戴氏父子(戴逵、戴勃)到一代现实主义大师李公麟,下及明清时期的黄山、新安画派,也都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
第三,皖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皖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区域发展极不平衡,文化发达的地区明显集中,并在时间上由淮河流域逐步向皖南倾斜。从春秋战国到西晋灭亡,皖文化的发展主要局限于淮河流域。寿春、沛郡、谯郡都曾经是皖文化的摇篮。这一时期颇有建树的安徽学者差不多都出生或生活在这些地区。公元317年,司马睿南渡建立东晋王朝,皖文化发展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长江沿线地区开始登上学术舞台。这时,我国的文化中心也转移到长江流域。而两淮地区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及战争的破坏,其在皖文化中的重心地位也开始丧失。隋唐北宋大统一时期,两淮的经济、文化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已失去了往日的勃勃生机,而长江沿线则人才辈出,产生了张籍、杜荀鹤、李公麟、陈翥等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公元1129年,两淮地区被金兵占领,从此,两淮人民先后沦入金、元铁蹄之下达140多年,两淮文化再次受到毁灭性的破坏;而皖南地区则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徽州地区异军突起,从事实上确立了其皖文化中心的地位,甚至在我国学术文化最不景气的元代,徽州一地也略显生色。明中叶以后,皖南地区更是人才辈出,在哲学、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均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清代,新兴的桐城文化与徽州文化交相辉映,将皖文化推向高峰。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徽州经学、桐城文派仍然雄风犹存。
三、皖文化成因的历史思考
那么,皖文化的成因如何?我们认为成因是复杂而综合的,但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安徽经济的发展来决定的。在人类历史上,先进的文化总是建立在较发达的经济基础上。皖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淮河流域,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新石器时代,淮河流域的农业就已达到相当水平,萧县发现的饮酒用具(陶规鬶、陶杯),说明当时的粮食生产除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外还有剩余。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两淮农业进一步发展,副业生产也受到重视。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楚两国曾因钟离(今凤阳)边境儿童采桑而引起战争。从1958年寿县楚王墓出土的鄂君启金节记载的内容以及楚国迁都寿春后使用的多种货币来看,战国时,两淮地区的商业贸易也很发达。而这一时期的安徽中南部还停留在“火耕水耨”的生产水平上。因而,皖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淮河流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秦汉以降至西晋灭亡以前,安徽地区的经济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即使在汉末以后,江淮大地上烽烟不断,但安徽经济也断断续续地获得发展,且其经济建设的重心仍然在淮河流域,西汉武帝两次移民江淮地区,东汉王景修复战国水利工程芍坡,开安徽屯田之先河,魏晋先后在两淮地区大兴屯田,开辟和兴修了大批水利工程〔12〕。因而,这一时期皖文化的发展主要还在两淮。公元317年以后,两淮由于战争的破坏,人口流失,经济发展停滞。安徽经济重心向长江流域转移,南贫北富的局面迅速改观。芜湖、宣城成为重要的商业都会。《隋书·地理志》中描写宣城:“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所以隋唐以后,皖境长江沿线人才济济。公元1129年,宋高宗迁都南下是安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历史分界线。淮河流域经济在金、元统治下一落千丈,皖南地区则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在明中叶以后,皖南手工业不论在生产技术上还是规模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芜湖的冶炼、染织作坊已具有资本主义工场的雏型,徽州纺织业也可与常、扬两州媲美,而且出现了原始形态的手工工场;徽商经过南宋时期的发展,至此已雄霸中国商界。因而,南宋以后,皖文化的发展主要在皖南地区,桐城一隅至清初才繁荣起来。
此外,安徽特殊的地理位置、我国政治中心的变迁以及与此相关的战争等因素,也制约着皖文化的发展。
安徽地处我国南北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大多发生在这里,因战争引起的政权对峙也是以江淮为界。数千年以来,华夏神州经历的种种风云变幻无不在江淮大地上引起强烈的激荡和反响。
一方面,由战争引起的国家分裂、政治中心的转移,直接促成了皖文化重心由淮河流域向皖南地区转移。秦以前,淮河流域较早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并形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汉至西晋期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淮河流域因毗邻国家政权中心,又是汉魏政权的发祥地,因而易得风气之先,而长江两岸,尤其是皖南山区则受惠不多,从而形成两淮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东晋和南宋两次政治中心南迁是皖文化中心转移的两个临界点,且这两次重大历史性事件都有十分相似的特点,即都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引起,都导致了安徽地区长期分裂。公元317年司马氏集团南渡后,安徽地区陷入分裂达270年之久。公元1129年宋高宗迁都南下到公元1275年元军占领大江南北,其间也有100多年南北政权的对峙。在南北分裂期间,淮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均遭到巨大的损失。而南方,尤其是芜湖、宣城一带则因为北方大批劳动力、先进生产技术和文人集团的南下,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同时,北方政权南下后,为巩固其地位,不得不在南方学术文化发展方面投入较多的精力,以实现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有效控制。例如,宋代安徽书院有19所,多为南宋时所建,其中有14所在皖南,仅徽州就有11所,特别是南宋理宗还亲自为皖南紫阳书院(歙县)、天门书院(当涂)和八桂书院(贵池)题额〔13〕。因此,政治中心的转移是皖文化中心转移的直接推动力。
另一方面,长期的战争和分裂,也造就了一代代安徽学人的特殊风格与皖文化的基本特征。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战争给两淮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从礼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去思考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设计理想的社会模式,并升华为对宇宙生成及万物本源问题的研究。道家思想是对春秋战国复杂社会现实反思的结晶。汉末至魏初,军阀混战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也给人民生活带来无尽的苦难,同时又为封建文人创造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因而,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既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又表达了一代学人渴求建国立业、统一天下的理想,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建安风骨”。《文心雕龙·时序》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两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短暂统一外,安徽地区基本上处于南北政权对峙的前哨,长期杀伐与统治者的疯狂搜括,使安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又无可奈何。于是,道家思想为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聪明睿智之士更是沉湎于玄虚之清谈,或攻艺事以为消遣。南宋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安徽地区则是抵抗金、元南下的主战场,因而以朱熹、张孝祥等为代表的安徽学人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的光芒。明末清初,农民战争与民族战争交织在一起,因而产生了一大批像方以智这样具有民族气节的伟大学者,经世致用也成为安徽学人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
(责任编辑 陈军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