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10004
- 积分
- 26016
- 威望
- 101310
- 桐币
- 55182
- 激情
- 107370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51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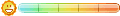
管理员
  
- 积分
- 26016

 鲜花( 130)  鸡蛋( 5)
|
|
明巡抚赵釴墓考 9 R) ^1 T5 r; R9 B* k
文 / 张泽国(大泽无水)
; N4 ~) x: D& q U$ o: C 县城东北三十里的麻山河西之阳,有一个叫墓园的地方。这不是一个虚拟的地名,而是确有一座大墓,当地人称之为赵家大坟。近年来,该墓因年代久远且规模较大而名闻遐迩,因此频遭盗墓贼光顾。今墓地荒芜,除零星残留石件外,余则荡然无存。至于墓主其谁、墓葬何时、毁于何代等相关情况,今天无人能说清楚,地方文物部门在两次文物普查后亦未做出相应结论。近闻赵氏后裔欲谋此事,提出墓主疑为赵釴之说,并声言如经核实,将申请启动修复计划。余闻之感服,主动介入其间,亦图通过调查考据以求证墓主身份,为该墓的文物保护与抢救性修复尽点绵薄之力。
9 s6 N: r6 W8 B7 m) c赵家大坟 ) o; q: h) \5 ^ S9 F: H
一.赵墓规制与赵釴身份相吻合
+ @) p, o( |( m: a/ ]7 L9 L2 Z4 y 如若认为该墓系赵釴葬地,那首先就要了解历史上的赵釴其人。据《桐陂赵氏宗谱》及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载,赵釴(1512-1569),字子举,一字鼎卿,号柱野,晚年又号八柱野人、瓠园丈人。明正德至隆庆时桐城人。始祖赵藻,南宋末由江南泾川迁桐,定居桐邑清净乡(今枞阳县周潭镇)之牛头山下,世称桐陂赵氏。父赵弼为九世,躬耕养母,有隐德。赵釴生有异禀,举嘉靖十九年乡试第一,二十三年进士。历事刑部主事,礼、吏科给事中,南太仆寺少卿,晋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贵州为蛮荒僻远之地,多苗彝等少数名族。赵釴宦黔久,平逆乱,问疾苦,导民礼义,政化流闻。教民引水为田,黔民知水耕自是始。后遭忌调南京,遂告归。居数年,隆庆三年卒,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旨“谕祭安葬”(《桐陂赵氏宗谱》)。南京户部右侍郎、前大理寺卿、经筵侍讲官桐城盛汝谦撰写《中丞公行状》,吏部右侍郎、前太常寺卿、管南京国子监祭酒事华亭林树声撰刻《中丞公墓志铭》,隆庆六年,名儒鄱阳史桂芳题书《中丞公墓表》。从赵釴生前身后的个人简历可以看出,其身份地位、葬仪级别及墓葬规制的等级之高。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赵家大坟的墓地上还散落有石狮、供桌、香炉等体量较大的墓表石雕装饰物,近来墓园周围还有大型石坊构件的新发现。考诸明朝官制,各省巡抚一职均由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担任,“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嘉靖四十二年,裁革总督,令巡抚兼理湖北、川东等处提督军务”。(《明史.职官志》)时任贵州巡抚的赵釴,是总管一省并兼管周边地区军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按《明会典》规定,正四品官员,其葬制可配有“石虎、石马、石望柱”等墓表装饰物。从墓制规模、墓园体量以及残存石雕件的数量规格看,应与赵釴卒后享受谕祭赐葬的品秩标准相近。从家族角度看,考诸《赵氏宗谱》,赵家历代先祖均无出其右者,以官阶品秩论,唯赵釴可享此殊荣。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该墓的规制级别与赵釴的官阶身份相吻合。
& `: h" Z3 K6 N+ \+ s' Z
: W$ d: N$ i- X: T墓地石狮
; {! S' m% C5 @5 ` 二.赵釴晚年活动中心在其葬地石鼓山周围+ A% g, o4 S8 \ ~" ^& L
赵釴墓地系生前自选,他选于何地,又为何选择这个地方,与其晚年生活有无联系?顺着这个思路,简单梳理一下赵釴退居以后的生活轨迹,看其中能否找到答案。 赵釴告老还乡伊始,于县北杜鹃山麓(注:按赵釴《宜秘洞说》,杜鹃山在城北便宜门外柴巷口之北。)置义田一区,“治圃于桐陂祖茔之北,(注:据《桐陂赵氏宗谱》载,赵釴祖父敏敬与妻陈氏,‘合葬桐城县城后道观山金盆地'。)把锄薙草,抱瓮汲泉,题其室之楣曰‘柳门竹径,学隐未迟。橡饭菁羹,谋生易足。’遂自称为‘瓠园丈人’”,从此开始了怡然自乐的田园生活。“公雅好佳山水,桐之龙眠山、浮渡山(今枞阳浮山)、麒麟山,有暇辄裹粮肩舆而往。酒酣意惬,蹑磴如飞,人罕及焉。”(盛汝谦《中丞公行状》)他常邀诗友同游,还“尝制油幕为行亭”,即特意制作了防水旅行帐篷,不论阴晴雨晦,携子或友,日游一山,徜徉山中,赋诗饮酒,题书刻石。在龙眠山中的宝山湾,今日尙可寻得八柱野人当年寄情山水的游迹仙踪。湾内小冲曰“百步绕云梯”,谷底称“云门”,岩瀑名“璎珞”,沿途石径、谿畔、崖壁间散落有“云门、龙眠处、听泉、清凉处、璎珞岩,海潮音、云根”等多处刻石题书,落款“鼎卿”、“柱老”,即当年的巡抚大人是也。(注:赵釴留下的“百步绕云梯摩崖石刻”,上世纪九十年代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g7 m, n4 X( ?: Q% p8 f7 L0 Z! F3 [
, s5 a" F' J) O赵釴龙眠山云门石刻
4 N7 ~' n% t" P0 V 在其游历的本邑诸山中,赵釴最爱的还是北乡的麒麟山。他在《助山堂叙》中写道:“予有一区,在麒麟山中,见高峰叠嶂,四顾墙立,而竹树骈植,苍翠相辅。意其中必有人不及知者,因令土人为道,日游一山。见笃山之孤特,小龙之峭丽,麒岭之崔嵬,石鼓之蜿蜒,莲花峰之高秀,舞蹈岭之徊翔,元元峡之郁盘,龙门冲之幽深,虽不能与名山争胜,亦一方伟观矣。因为堂于石鼓山下,尽揖群山而友之”。赵釴以麒麟群山为友,专此建堂驻留,足见其笃爱之深、钟情之甚。 为何作此选择,其《偕乐亭记》一文中能找到答案。赵釴认为,邑中名山,东南浮渡山、白云岩、大小龙山太远,龙眠山太深,凤凰山(即投子山)太峭,“游者岁不能一至”,而“一方伟观”之麒麟山则较为适中。
8 b7 d, I8 r. p 岐岭风光之胜,邑中名贤亦多有撰述。清代散文大家刘开路过此地时,曾就撰文以纪之。他在《过岐岭记》中写道:“未及山半已尽川原之胜,升高以望,百里内外近在咫尺。踰岭以西,则舒城众山出焉。岭之左曰莲花尖,小龙峰之所依倚也;岭之右曰刘氏寨,元明纪家冲之所避乱也,皆与岐岭连峰相接,势均力抗,不为稍下。其余诸山尽为培塿,争若俯首听命。山故有寨,叠石为门,甚狭而峻,常有云气生于山巅,雨露之所滋,流泉之所泻,虽晴霁地亦湿焉。”先贤笔下的麒麟山色如诗如画,但其具体地点又在哪里,赵釴当年的旧迹遗踪究竟有无线索可寻呢?
4 U" ~0 ~1 Z, b0 k5 \- k2 C, @ 经查清道光《桐城续修县志》,赵釴游历的麒麟诸山,原来都有出处。麒麟山位于桐邑北乡,其区域大致包括鲁谼山以北、大关以南、麒岭以东、金山以西的大小山峰以及山冲、过峡,面积约近十平方千米。其中小龙尖、龙头山、莲花尖、麒岭、蒋山、笃山、大过峡、龙门寺等地名志书中都有记载,古今一致,极少失传。为求证其所在,近日随明伍、晴川先生等赵氏后裔至当地踏访,欲就方志文献中涉及的地名实地予以确认。
4 Q0 z3 }6 Z. o R6 T% V$ X: }" T! w* |# c
麒麟山远眺 $ g: ~( W) {$ O% b* X% j
从三十里铺西行不数里,即墓园,园区居小邱之上。经当地耆老姚佐庆先生指认,赵釴当年游历的麒麟诸山尽在眼前,史料记述与实境地形相合。由坟地西望,平野开阔,群山环抱。西南一峰为小龙尖,前有舞蹈岭(衍名“五道岭”、简称“五岭”),后有莲花峰;正西为麒岭(即“旗岭”、亦作“岐岭”),为麒麟山主脉,峰峦耸峙,高峻崔嵬;其北为大过峡(疑为“元元峡”),穿峡为龙门寺(即“龙门冲”),东折为笃山;由麒岭东南分脉之平邱,即至墓园之山。
& g/ Y! m7 }2 W0 F! S" u& U7 x4 N8 H* }, ]: v
小龙尖 4 {& D$ _; C0 q- Z5 m2 R4 B/ o
赵釴《助山堂叙》中列举山名,大多能一一对应,唯有“元元峡、石鼓山”二地,方志不载、当地无传。结合《县志》、《堂叙》有关此间山势情状之描述,再经实际地形相比照,基本可以判定,龙门寺以南的大过峡即为元元峡,麒岭东南蜿蜒迤逦之平冈就是石鼓山。笔者推定石鼓山具体方位,依据有三:第一.方志中山川地理记述、赵釴本人描述与实际地形相吻合。麒麟诸山,特色各异:或孤特、峭丽;或崔嵬、高秀;唯石鼓山地貌有别,蜿蜒平迤,中有圜丘极似鼓形。虽山名已佚,但山形可辨。第二.按《桐陂赵氏宗谱》赵釴辞条记载,赵釴葬地“名墓园”(亦即墓园今址、赵墓所在),与《中丞公墓志铭》“葬公于石鼓山之阳”的记述相互印证,石鼓山地名不言自明。也就是说,赵釴《助山堂叙》中记载、而后世失传的石鼓山名,因《宗谱》和《墓志铭》中记述以及实际地名相互参证可以重新确认。第三.墓园所在的助山堂遗址,亦可佐证石鼓山的具体方位。经当地走访调查,据村民反映,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的生产、建设过程中,就在他们居住的村庄下面,不断出土的砖石类古代建筑材料无以数计。村庄即在墓园之后,几乎连为一体。据赵釴《助山堂叙》记述,“堂成于嘉靖乙丑九月(1565)”,“为堂于石鼓山下”。由此可见,今日的墓园村庄应该就是当年的助山堂遗址,堂址、墓地所在之山就叫石鼓山。据此笔者推测,当年赵釴撰写《助山堂叙》的地方应该就在助山堂,文中描绘麒麟山诸景所取的角度,大概就在墓园今天的方位。至于石鼓山之名缘何消失,疑其原因有二:一是赵釴葬后,其地即以墓园名之,久之逸其山名;或因明末战乱,墓地建筑遭毁(注:笔者据方志史料及墓地状况推定),园区陵替,地以人传的石鼓山名随之消失。二是此地称金山,早在北宋时期,当地就有“金山寺”佛教丛林。据道光县志记载,金山寺为宋琇禅师建,明洪武时僧善觉重修。(笔者注:从当地调查得知,该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撤除,其建筑材料改作金山小学建校之用。)石鼓山名随墓园荒颓而消逝,也有可能与金山佛寺的盛名掩蔽有关。# `) ^ n; o' U, t7 ]
综上所述,从谱、志记载与实地调查相互印证的结果看,赵釴晚年生活的区域就在石鼓山周边的麒麟山区,其当年的助山堂遗址及葬地就是今天的墓园所在、即已逸名的石鼓山。由此笔者认为,位于此间的赵家大坟,实际就是明代巡抚赵釴的墓地。# n4 R# y; N3 [# N. W9 B
7 P& o) g8 l/ X9 X6 T
石鼓山 # p# ]5 i( A) g( \9 X. A
三.墓葬型制风格符合墓主生前的性格特征
) k8 O: j2 k, G+ ? 今墓地尙存一碑石,上有“乐矣天也命也”文字一行,竖行楷体、书法清润,平膛阳刻、笔迹清晰。从残碑大小行状看,似为墓门碑联之下联。自刻诗碑之墓葬型制桐城确有个例(如清本邑练潭布衣诗人徐翥、吴鳌两墓),但自题墓联之类型笔者却未曾见。这种奇特的墓葬形式与墓主有无关联,联文何人所作,想表达什么意思,解开其中之谜,对进一步确认墓主身份应该说非常必要。
0 }; ~2 `+ ` F0 j! L: f
/ O S" b, y; L3 |7 O墓联石刻
2 E' L# \- y9 W3 |3 L 在前文的叙述中,已经勾勒出赵釴人生的大致轮廓。赵釴既为名宦,又是通儒。生平博览群书,学养深厚。“为文章自出机杼,精光百倍”(《中丞公墓志铭》),“为诗多写其潇洒出尘之趣”(《中丞公行状》),诗律清远。但赵釴所治之学,并非其时朝廷推崇的正统程朱理学,而是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的心学。其学以致良知为宗,知行合一。赵釴退居后,罄俸银建祠堂,置义田,济乡党,而自奉淡如。性旷达,喜交游,因爱石鼓山之境,筑堂羁游,招“好事者乐余之乐。往往有欲游者,则迎致之;其欲游而不能游者,则强致之;游而不欲去者,则慰留之”。(《助山堂叙》)终年以山为友,乐此不疲,心无旁骛,返璞归真。最能体现赵釴性格特征的还是他的人生观、生死观。其于石鼓之山,“营寿藏其上,题曰‘俟邱’,取修身以俟之义”。(《中丞公行状》)他自选墓地,并不是看中什么龙脉,以为后代子孙计。而是修养身心,静候以待归藏。隆庆二年,还特意撰文自祭,以表心迹。他在祭文中强调,所谓堪舆之说鲜有一验,不可卒信。认为人生于土,卒返于土,土皆可生,亦皆可藏,哪来龙脉吉壤、风水宝地之说?他写道:“惟兹一丸之土,实在万山之中,本无奇形,亦无异穴。但岁时耕于斯,云霞自足;料他日老于此,魂魄亦安。吾知山川有待造化,无私山灵必不拒吾,吾亦不负山灵。吾有古书一腹,仁义一腔,山水眼一双,掞天口一张,诗酒肠一丈,观化之目一副,将来与山林出入于清泉白石,徙倚于修竹茂林,无古无今,任来任去,不亦乐焉!” 对于人与自然、生命本原、人生价值的认知与探求已然趋于化境,几至天人合一、心鹜八极的神游境界。他将自建的助山堂作为人生最后的游弋清修之所,将自营的俟邱视作与麒麟山相伴的永久驻留之地。“乐矣天也命也”的墓联涵义,不正是赵釴乐天知命、潇洒旷达的性格特征的真实写照吗?由此可知,如其自选俟邱、自作祭文一样,墓联亦应为赵釴生前所为。另在墓园西北之笃山,也有一景疑与赵釴有关。此景曰“仙人对弈”,居笃山之巅。有石刻棋盘及文字,文曰:“黄粱熟未、赤壁乐乎”。楷体阴刻,字径寸半大小。笔者于四十余年前曾亲见,今寻未果。仅凭记忆推测,若从书法字体、文字涵义及题刻地点来看,颇似当年赵釴所为。2 |( C9 C8 E/ `. S/ U# H* R8 z
/ {% ^& b" E+ I6 _ 四.墓地山向及残留文物可以确证赵家大坟即赵釴墓
) U4 s7 |" Z7 A4 P$ X, Y7 | 据《桐陂赵氏宗谱》赵釴辞条记载:“继殁,奉旨遣安庆府知府査志隆谕祭安葬于斯土,名墓园,寅山申向。”家谱所载墓地山向应是墓地确认最为可靠的基础性依据,经墓园赵家大坟现场勘验,谱牒中赵釴墓“寅山申向”的记载与墓地朝向完全相合、毫厘不爽。至此可以结论,赵釴墓已确定无疑。问题讨论到了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但有一个疑问却一直未解,那就是赵釴葬后的四百余年间,其偌大坟地及坟山地名等历史信息为何失传,以至消失得无影无踪。笔者试图从现场遗留的石刻残件入手,探寻该墓的历史盛衰,还其本来面目。$ O W/ B( Q; W8 F) @# l
赵家大坟名不虚传,从墓地朝向看,视野开阔,气势磅礴。从整个墓区占地面积看,不下数千平米。墓冢位于石鼓山之巅,冢径约二丈。墓区顺山势走向自东往西平缓递降,长度百余米。从墓区地表及周边散落的石雕残件看,有石狮(二只)、石墓联、石香炉、石供桌、牌坊石柱、夹杆石等。由当地走访得知,新近发现的两根牌坊石柱,原本不在村庄之中的出土地点,是被人数十年前从墓区搬移挪位的。其中一根较长的坊柱刻有联文,可识者“宗清派洋洋绵氏族”八字,楷书阳刻,字迹工整。这些石质文物均为墓表装饰物,按其类型分,墓联残件应属墓冢建筑构件,香炉、供桌为墓前石雕祭器,石狮为墓地石像生,牌坊则是墓表体量最大的标志性建筑。无论文物构件单体还是墓区石雕装饰物整体,都呈现出体量较大、造型厚重、线条粗犷、风格朴实的明代特征。
4 J& @: C/ @8 A! l* u% K9 z' _ {( g" y; A' m$ \2 H/ {
牌坊抱鼓残件 " ^3 E/ |1 B! c9 p! f. [
若从《桐陂赵氏宗谱》提供的文献资料看,墓地建筑似应还有一件重要的石质文物“中丞公墓表”。墓表与墓志互为表里,一个墓上,一个墓下,其内容都是记载墓主生前主要事迹。墓表、墓志文字均由名人撰写,它既是古代散文的一种文体,又是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葬制的一种既定形式。墓表与墓志不同之处在于,墓志与墓主相伴藏于墓中,墓表则立于墓上,供后人凭吊瞻仰。赵釴葬后第三年、即隆庆六年,赵釴之子赵鸿赐托人千里致书,专请名儒史桂芳(曾为赵釴同僚、挚友)为其父撰写墓表。鸿赐,字承先。好古笃行,集士子为陋巷会,衍阳明良知之旨,学者称枞江先生,为当时名士。鸿赐延请名儒撰拟墓表的目的,就是为了刻石铭碑,将其树立于墓地之上。后经走访获悉,当地人称刻有诸多文字的大碑(注,应为墓表),毁于抗战期间的敌机轰炸,其后残存碑石逐渐散落于周边村庄。在当地的多次走访中,对于整个墓区原貌何样、毁于何时,当地人亦莫知所之。综合该墓古今情状及石雕构件残损风化程度分析,笔者推定,墓葬整体遭毁时间应该不在近现代,而是明末时期。$ z# V, f2 I- s0 E
" z4 N% Q9 c {5 z( B0 j. ^& m) v
牌坊柱联文字
8 X+ p: I& U0 f& w% ?6 x4 ]3 ^ 据《桐城续修县志》记载,自明崇祯八年正月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犯桐以来,直至明亡的十年间,除县城以外,四乡之境几乎沦为起义军之手。民间建筑物大多毁于战乱,荡然无存,明朝官员的墓地更是首当其冲。从本地不可移动文物的调查资料看,明代以前名人墓葬的地表建筑均遭毁坏,像汉代大司农朱邑墓、明代貤封监察御史盛仪墓、四川按察使余珊墓、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墓等,无一幸免。由于赵釴墓地损毁严重,刻有文字的墓碑、坊表散逸殆尽。久而久之,后人不知前事,最终导致墓主无传、山名消逝。搞清了石鼓山墓园的前世今生,也就不难理解清道光县志中,只有赵釴城中“解元进士”、“桐冈五凤”两座牌坊的记述,而莫知其葬地所在的真正原因了。
) f- W) ?& W5 K 赵釴是明代桐城地域文化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墓园也是桐邑北乡重要的人文史迹、风景名胜。其人其墓虽然沉寂了四五百年,但其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依然存在,仍然能够为当今的社会发展服务。期盼在不远的将来,石鼓山下的助山堂、墓园与麒麟诸山一起,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再现昔日那风光无限的奇特魅力。2 e- T& X, |5 v3 I4 K' x
0 Y3 w2 z0 P% W0 N
张泽国 2017年5月于骏园
, Y( B5 b- v3 Y2 g% ` j N/ O: f2 v9 i1 j" \0 c. |! Z# A
& m" G! r. e, l! M5 U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