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56560
- 积分
- 1917
- 威望
- 1046
- 桐币
- 251
- 激情
- 4621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1472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10-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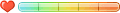
桐网嘉宾
 
- 积分
- 1917
 鲜花( 27)  鸡蛋( 0)
|
本帖最后由 同安闲人 于 2012-5-18 10:54 编辑
4 O; Z! a: o& g- c( [8 \' P" `. o% I5 j' Q$ Y+ V2 v! |
戴名世:桐城派开山鼻祖
' O9 L2 g) C6 r" m/ X7 { W作者:一滴残墨 2 f( c% t( ?' |" D4 @# O- S" w
安庆一带,尤其是在毗邻的桐(城)、怀(宁)区域,只要一提到“桐城派”,人们脱口便道出戴名世、方苞的大名。尽管戴氏因文字狱罹难,人亡书毁,株连文友亲朋,以致学人忌议,世人避讳,但家乡人对他的爱戴和赞美之情始终如一。这除了生养万物的土地总是厚爱自己的儿女外,戴名世本身那勤苦潦倒的一生、愤世嫉俗的性格、正气凛然的古文创作,振兴古文的新颖理沦和反对科举、时文的叛逆精神等,都给后世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怀念。他作为桐城文派开山鼻祖的“一祖”形象,将永远屹立于历史的沃土之上。然而,迄今仍有学者持戴名世非桐城派作家的观点。因此,对戴名世“这一个”个案作进一步研究,仍然很有必要。- e: b9 _9 A* o8 ?7 [
$ d6 ^! c+ M7 W c' N1 @
生平与性格 戴名世( 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世人又称之为“南山先生”、“宋潜虚先生”。称其为“南山先生”始于他50岁时,因这年他在桐城家乡南山冈置宅,且著有《南山集》,故以其居处和书名称之;康熙五十二年他60岁时,因《南山集》案被清廷处死,为避残酷株连,世人隐其真实姓名,才称之为“宋潜虚先生”,此乃取“宋为戴族所自出”之意,其姓名均系虚托。% A- g$ m" I9 w3 W! q7 | Z8 a
[3 R. ^" C. X2 p) \ 戴名世出身于没落的官宦书香门第,始祖于明末自婺源迁桐城。祖父古山曾在江西为官,父硕却一生授徒,家境贫困至极,但忠厚为人的家庭传统博得社会一致赞誉。戴氏在《先君序略》中说:“家世孝悌力|田,以赀雄乡里。里中皆称戴氏忠厚长者,县大夫辄尝馈问,以风示县人”,称其父“为人醇谨,忠厚退让,从不言人过失,‘与人交无畛域”,但终因艰苦备尝,又性不喜家居,48岁即病逝于东乡陈家洲馆次。陈家洲百姓泣呼:“天无眼矣!”戴名世则哀叹:“呜呼!人莫不有死,而先君客死,早死,穷死,忧患死,此不肖名世所以为终天之恨,没世而不能已者也。”此时28岁的他,受到极大的震撼,其后的愤世、犴悖性格的形成,当与此有很大程度上的因果关系。
( i" p& j5 T5 B1 I: t$ [% p* q* U: `- g
戴名世少而多病,却聪明好学,智力超群。6岁从塾师受学,l 1岁即通读四书五经。24岁到34岁这十年间正值青年时代,他除从事古文写作外,主要是教书、写时文和考科举。康熙十九年28岁时,即被“以国士相目”补为秀才。33岁以廪生得选拔为贡生,34岁那年冬天,他又以文行兼优的贡生资格赴京入国子监肆业。这十年间,他创作大量散文,出版了专集,得到广泛赞誉。3 5岁至50岁这1 5年的壮年时代,他京试落第便遍历南北各地,以卖文养家糊口.同时为写明史广罗材料。在其《北行日记序》中描述道:“往余居乡,以教授糊口,不出一百二百里之内,岁得一锾二锾,与村学究为曹伍。计四时中省亲一再归,归数日即去,虽无安居之乐,亦无行役之苦。后以死丧债负相迫,适督学使者贡余于太学,遂不得已而为远役,则始于岁丙寅之冬.距今十五年。往返奔走,遍历江淮、徐泗、燕赵、齐鲁、闽越之境,凡数万里,每行辄有日记。”他将卖文所得存于友人赵良冶所者凡千金,在家乡买下南山冈田五十亩,并建宅室,题堂额曰:“砚庄”,准备终生隐居。然“家众凡十余人,皆游手惰窳,不谙种植。岁收所稻,仅足供税粮及家人所食,而余遂不能常居砚庄”。生活迫使他无法安居乐业,每年二三月即出游于外。自51岁至60岁被害,是他晚年时期。这十年间他往返于砚庄、金陵、姑苏寓所,从事八股文的编选以谋生。53岁和5 7岁时,他还先后考中举人和进士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59岁即遭御史赵申乔参疏,被捕入狱,于60岁那年的二月初十被处死。
7 N5 p. ?1 O M4 P+ [% P; Y3 L6 ?. t5 U9 e/ f
纵观戴名世多舛的生平,不难窥见其思想性格上的主要特征。由于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他“少而狂简,多幽忧之思”。其父也是才子,“为文嘱草,步阶前数回,即落笔就之,不改窜一字”,然屡试不第,穷困潦倒夺去了他年仅48岁的生命,这对戴名世是“终天之恨”。其父生前见他好读书但不识时务,预他日后将同自己一样难以维计。他青年时代即“厌弃科举,欲为逸民以终老”,而“家贫无以养亲”,迫不得已在20岁时即开门授徒。虽对封建时俗强烈不满,却不得不从事时文(八股文)的传授,这就使他内心产生矛盾,极端痛苦而又不能自拔。因过多过度的“幽忧”,而致桀骛不驯的“狂简’’,此实乃为当时社 会所造成的一种“独特”。他将居室命名为“忧庵”,并写有《忧庵记》.既是对自己境遇的写照,更是对社会问题的忧愤和无奈。9 ^# z% Q. U9 L( r
+ U3 W) X" ?1 G, d6 X
戴名世终究是强者,他在《与弟书》中写道:“丈夫雄心,穷而弥固,岂因一跌仆而忧伤憔悴,遂不复振耶!”他愈困愈倔,愈傲愈斗,于治学为义上执著追求,顽强探索,以实现他振兴古文的人生理想。如果说他“少而狂简,多幽忧之思”终属其性格上的软弱,那么,他这种知难而进的追求和抗争精神,无疑是他性格上的最亮点。9 e2 l+ M. D% f' k, u
- y4 Y$ O! R" j/ B6 c' g2 i, x 戴名世高傲嫉俗的天性,决定了他好作愤世嫉俗之古文和酒后论世的放肆,故时时招来世人责怪和非议。《清史稿•戴名世传》说他:“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一介寒士竞遭到世人诸公如此畏惧和忌恨,最后被加之“大逆”罪处死而后快,也就似乎“顺理成章”了。封建主义的专制性和残酷性,造成了他必然的悲剧结局,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5 F6 D1 K# Q* G- j# g
; Z( P q$ |( k" F 戴名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是他在痛恶人之社会的同时酷爱自然.,性好山水。他在《数峰亭记》、《游大龙湫记》中,均反复提到“余性好山水” 他以“田”、“褐夫”为字,并作《田字说》、《 褐夫字说》,乐以鄙自居,视贵贱尊卑为粪土,可见对丑恶社会现实的厌恶。对自然人性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是他作为一名进步文学家有别于当时一般人的独特品行,实在是难能可贵。然戴名世终究是封建社会的戴名世,他有悖于王朝的“大逆”,招致的只能是杀身之祸。这不仅对他个人是无法避免的悲剧,同时也是对其后的方、刘、姚“三祖”及整个文坛的严酷警示。于是揭露、鞭挞社会的作品士者不敢问津,原因很简单:谁也不愿意自投罗网,重蹈《南山集》案之覆辙,做戴名世第二。这应该也是当时不敢尊他为桐城派“一祖”的主要原因。' q* o! n J& Z" c" q8 j
/ c- r; o: m. h! N8 O* `
创作与文论 戴名世好为古文创作的习性自少年开始。他在《自订时文全集序》中说自己“少而多病”,“病有间,因穷六经之旨,稍见端倪,而旁及于周、秦、汉以来诸家之史,俯仰凭吊,好论其成败得失,间尝作为古文,以发抒其意”。青年时期,其散文创作已颇有成就,仅24岁至34岁这十年间,即著有《芦中集>、《天问集》、《困学集》、《岩居川观集》等。壮年时代,他京试不第便遍游南北各地,以卖文为生,行程数万里,“每行辄有日记”,并为日后编写明史搜集资料。在他4 9岁时,弟子尤云鹗为他刻印了《南山集》,收古文百十余篇。时至晚年,仍为衣食煎熬,一边编选八股文以谋生,一边应乡试、会试,并编订《四书朱子大全》。5 9岁遭参入狱后仍在修订《四书朱子大全》,直至60岁时因《南山集》案发被处死才搁笔。我们说他为古代散文创作,为实现其崇高理想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样是最恰当不过的。. C5 m. L0 ], E
! f+ J U7 b% v. M/ }6 g- q( P
戴名世的主要成就是在古代散文创作上,自称:“田有自少学古文。”他极力反对时文(即“制义之文”,又称“八股文”),在《甲戌房书序》中说:“所为时文之法者陋矣,谬悠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此竖儒老先生之所创,而三尺之童子皆优为之。”可见在戴名世眼里,时文是“谬悠”、“腐烂”,既“不通于理”又“不适于用”,只因科举应试之需要,连“三尺童子”也难免深受其害。对时文的弊害有如此清醒的认识,那他为什么还要写时文、教时文呢?他自己道出的原因是:一因“家贫无以养亲,不得已开门授徒,而诸生非科举之文不学,于是始从事于制义”;二因他认为世人既把古文、时文划分区别为两种不同的文体,那么作为一种文体的时文必须有其一定的作法,而这种“法”浅陋、谬悠,悖理无用,束缚思想,磨蚀意志,贻害无穷,务须排斥之,改造之。如何改造呢?他在<甲戌房书序》中指出:“然则何以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可见他对时文是欲以古文来改造时文,一扫泛滥于文坛的时文僵化颓废之风。其友方苞在《南山集偶钞序》中也说,时文“此非褐夫之文也”。他是古文宗师,其门生尤云鹗说:“其所为古文较之制义更工且富,于是四方学者购求先生之古文踵相接也”。
?2 E! }0 |$ A" {% R7 e' D" h! {5 v! D2 w, j) D1 W) _* q
戴名世创作颇丰,生前自编和身后门人好友刊行的计有《芦中集》、《困学集》、《天问集》、《柳下集》、《岩居川观集》、《周易文稿》、《自订时文全集》、《意园制义》、《齐讴集》(诗集)、《南山集偶钞》、《孑遗集》和抄本《忧庵集》等,可惜大都散失。
1 ^) h. [% b' O @/ H& _7 Z+ C; ^- g6 k
从戴名世流传下来的2 82篇古文作品来看,绝大部分思想内容健康向上,具有旗帜鲜明的进步性,读来令人觉得正气凛然.酣畅淋漓.在深受激励、教益的同时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如在《杨维岳传》、《画网巾先生传》中,通过颂扬抗清志士的民族气节,表达了人们对变节投降的民族败类的愤恨之情;在《钱神问对》,《顾贞叟传》、《醉乡记》、《盲者说》、《河墅记》、《狄向涛稿序》等义中,对名为“康熙盛世”实为“败坏之世”的种种昏冥丑恶,包括科举之害、时文之陋,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揭露和抨击,而在现存的31篇游记中,作者又把祖国大好河山描绘得如诗如画,“且能融情于景,寓理于物,巧妙地把作者的人格与个性、理想与情操,寄托于他的游记描写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其作品思想内容上的直面现实、干预生活的自觉性和追求真善美的坚韧性,为后“三祖”方、刘、姚所不及,此乃广大读者的共识。6 {! _- s2 a: m4 s% O5 E0 R
1 a4 C& a/ P5 C
戴名世在古文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其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 一位古文造诣很高的儒僧,看了戴的文章说:“吾素闻当今文不雷同者,惟此人。”他即使跟许多著名的古文家相比,也是艺高一筹,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首先,他一改时文的“代圣人立言”.而主张“文章者莫贵于独知”,其作品具有“我之为我”的特色,第二,采用白描手法的技巧达到传神的效果,写实传神是戴文的一大特色。第三,文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篇篇锐意创新,别开生面。第四,率其自然,为文效法自然,追求自然本身之美,其作品严谨又不失活脱,形象饱满优美。他这种自觉地把握文学的形象性特征,进行神圣的艺术创造,是对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的重大贡献。
1 W' \ U H4 D ?& O8 w7 B
8 ^, M; L& p/ j4 [) [% D 戴名世为完成“振兴古文”的历史使命,“一洗时文之法之陋”,对于古文创作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新颖、可取的理论主张。他要求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指出此乃自古以来古文写作的共同规律。不只是在语言文字上要去“雕饰”,且要求文章的篇章结构即在文章的整体上,也要求自然畅达,做到“文贵自然,浑然天成”。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时文猖獗的年代,把“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作为散文创作最根本而不可背弃的原则提出来,却只有戴名世一人,尤其是“行其所无事”这后半句,更是自古无人道及。这种要求为文者彻底抛弃功利和人为的框框,完全按自然发展规律本身去写作,在当时诚然是一种超凡脱俗、颇为贴近近代现实主义要求的创作论,很富有民主性。
! S+ y" G W! g& e1 B, }' u7 J' n) Q9 s4 P h) a
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这一古文写作共同规律的统领下,戴名世的论文主张特别强调“言有物”,文章要有感而发,内容充实。在古文创作方法上,他要求“道、法、辞三者兼备”。他在《己卯行书小题序》中说:“道也,法也,辞也,i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他所谓的“道”自然指的是程朱理学之道,但他那率其自然的文学观点,坚持“我之为我”的“独知”原则,又使其创作出大量反映现实生活、揭露腐朽的作品,做了一位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的“大逆不道”的“这一个”文学家。他的所谓“法”,包括御题之法和行文之法两个方面,前者“有定”(八股文的同定格式),后者“无定”,“文成而法立”,视其内容灵活运用行文之法,以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他的所谓“辞”,即倡导 如《左》、《国》、庄、屈、马、班及唐宋八大家的“古之辞”之美,而摒弃“诸生学究怀利禄之心胸”的“今之辞”之恶,此乃实为后来桐城文标举“清正雅洁”的因由。在古文的艺术境界上,戴氏追求“精、气、神三者浑为一”之术。这一启示于道家养生之术的论文主张,是要求作家的主观修养、艺术构思乃至作品,在总体上所要达到的艺术境界。所谓“精”,他认为“雅且清”则精。作家唯具有良好的白身修养,才能在作品内容上弃糟粕取精华,然后才能在语言风格上达到清正雅洁。所谓“气”,指文章的气势。作家要有驾驭和超越客观事物的志向气质,才能写出风云激荡、气壮山河的作品。所谓“神”,指的是“对文章内容和形式的总体把握.要达到由表入里的‘真知’的地步”,“写出足以表现对象个性特征的神韵”。在向古人学习为文的承继性方面,戴名世的见解与做法也自有其独特和卓越之处。他说:“文章之道,未有不纵横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者也。”也就是说,唯有“纵横百家”才能“成一家之文”。同时他又指出向古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仿古、拟古,而是为了要有自己的独特创造,“成一家之言”、“辟一径而行”,他那别开生面的散文创作,正好印证了他的这些文学主张的可取性和进步性。当然,戴氏的古文理论尚显得系统性不足,但颇富开创性,为桐城派开了先河,“桐城家法”自此得以奠基。后“三祖’’的文论,诸如方苞的“义法”说,刘大櫆的“神气”说,姚鼐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等,虽日臻完善,形成了全面、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但均能从戴氏的文学主张中找出其一脉相承的依据。应该说,后者是前者的承继、拓展和深化,也是对历代古文理论的扬弃和总结。. I* K% Y$ {. q
3 m* J5 z; [, G/ e; [+ h7 K 毋庸讳言,戴名世是清代最负盛名的古文家,但他却没有应有的历史地位。他是桐城派的开山鼻祖,却长期以来被排斥于开“派”宗师之外。这是为什么?答案很简单,由于他在康熙五十二年因“《南山集》案”被处死,其文集遭禁毁,其姓名亦为人们所忌讳,残酷的株连更令学人士子谈“戴”色变,试想谁还敢斗胆冒统治者之大不韪,为他正名呢?然当清王朝日薄西山、苟延残喘的末期及至当代,持论公允欲还戴氏历史之“一祖”真面目者, 倒也大有人在。且列举数例,权作本文结语:( E# `6 S; V/ j7 d9 e0 `% Z2 V
( u& N# K+ K- s" o& b3 n' {
梁启超:“他本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推他为开山之祖。”(《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
7 @ y$ H% \- x
( _3 V- R- D; p% f$ K 柳亚子:“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论者谓其才学实出方苞之右。”(《南明史料书目提要》)。* x) @! z2 [7 O2 `$ R
" G ^3 B; Q' u# C 王凯符:“说戴名世就是桐城派作家,甚至以他为桐城派一祖,都是可以的。”(《戴名世论》)
' B, A' Y; L s0 q# N9 x5 j- E5 @. ~; d
周中明:“桐城派的文学主张是以戴名世为先导的……我们要了解桐城派文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貌,就绝不能抹煞戴名世为桐城派先驱者的历史地位。”(《桐城派研究》)
- K( Z# z3 o, z$ z" o7 n# ] # r) w8 j/ E' j- C% T- u7 r' Y
原创作品,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
评分
-
查看全部评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