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12493
- 积分
- 565
- 威望
- 9292
- 桐币
- 559
- 激情
- 24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14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5-9-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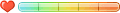
桐网嘉宾
 
- 积分
- 565
 鲜花( 0)  鸡蛋( 0)
|

楼主 |
发表于 2005-12-22 10:26:29
|
显示全部楼层
[size=1]转自《长线文学丛刊》
现代化进程中的戏本折射——关于陈先发的长篇小说《拉魂腔》
一 、小说形式的愚见
对于地域文化的表现,辅以词条或中心词语为分章标题的写作形式,有不少类似的版本。从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到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还有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等。有的学者称这类作品具有编年史作品的重要特征。在奈保尔获得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皇家学院的授奖词中,就有这样的话:奈保尔先生是继康拉德之后的又一危编年史作家。当然若再往前推,巴尔扎克老先生更是经典的编年史作家。
这类作品都有个近似的特点,那就是貌似纪实的文体,将一个地区的社会风貌、文化特点、人物生活和命运以块垒状的故事组合,逐层剥解,适时用以小人物的命运撬动故事情节的杠杆,从而演绎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悲剧风格。这种既独立又关联的故事集合,在一个小整体的叙事结束后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所以更容易牵引读者的胃口,而对心灵的触动也更持久、深重。这些优秀的文学探索成果,给当代文学范式扩延提供了重要基础。
作为淮河两岸的一门古老剧种连接于苦难的淮河人民,他们的生活和变迁,传统之于现代转变进程中的演绎,上述形式的表达也许正适合陈先发的长篇小说《拉魂腔》。
二、在遗忘传统的现代中与传统交手
读完了《拉魂腔》,的确是如一块湿棉花,洇在喉间好几天,终于得到吐出的机会。
小说让我看到一个多难多劫而顽固陈腐的淮河。而淮河风习就像一坛淹了千年老咸菜,被洪流冲刷千年也冲不掉那些根扎在人心中的身后积垢。对旧文化的固守,那里人们的顽固远非我们所能想象的。老祖宗旧时光千百年遗传给他们的风习和单一坚贞品性已经深扎他们骨髓,成为一种生活,成为他们活下去的寄托与保障。在现代性的洪流面前,他们宁愿过着不知魏晋的小民生活,也不愿加入改革的洪流随意动迁祖宗的地盘半步。最后,只有付出生命代价——祠堂被烧,村中灵魂人物麻三叔杀死亲子并自杀,可以说,只有毁灭了村庄的灵魂,涤荡了他们千年守卫的文化,才创造出得以抵达新生活的道路。这是现实还是必然,也许是困在每个关注中华文化心头的一个巨结。
如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系列抵抗当代生活的愚昧和顽固,但在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现代生活已不仅仅是符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洪流铺天盖地淹没整个国土时,实在太难想象地球上还有摊子村这样一个角落。但这都是真的。现在,需要我们这些在阔亮舒展的生活环境中,去想象这样的村庄,一个仍旧点着煤油灯,灾年年洪水肆虐下无所谓农业,靠捕鱼杀狗、捞洪灾物品为生的村庄。
这个叫瘫子村的低洼小村,让我想到了十几年前阅读的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同是安徽古老村庄,它们的讦倨个性和怪僻民风,着实让人诧异。尤其是对象征他们坚信的祖宗神灵、村中千年伺奉的诸如祠堂之类的守卫几乎到了狂烈地步,我想,这里面一定是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学意味的,那就是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汉文化圈内,宗法的信仰是作为他们精神寄托而出现的。瘫子村百姓齐心合力坚持要走的毁亡命运不仅仅是在暗示什么,已然扎根他们心中的固像化图腾,比任何繁华与富强更具吸引力。瘫子村那位唯一的文化人,七十多岁的神怪老人梅子孝的话,或许能给一些答案:“你们外面人把灾想得太可怕了。灾呀,我倒觉得像瘫子村人身上的毒瘤,都晓得它毒也愿意把它割掉,但这个瘤毕竟是长在自己肉里的,谁也没有把它看作身外的东西。再说啦,灾既毁了人也壮了人啊,你老弟仔细瞅臭,那些衣食无忧的繁华之地,有几个人不是意志萎靡消沉不振的?他们斗着灾,习惯了,斗着灾才像个人……”此番高论,不禁让人唏嘘。这就像对某物上了瘾,再读再毁人,可它是你身体里的一部份了,痛恨它,离不开它。
三、较量之后选择的可能
书中涉及的分明是关于传统与现代如何较量的问题。这的确是个困扰人类长时间的问题了。海德格尔几十年前就惶恐地讲:“当我而今看到月球向地球的照片后,我就惊慌失措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代人已经连根拔起,我们现在只还有纯粹的技术关系。”在走向现代的路上,世界经历了无数毁灭性的灾难,纳粹的暴行、两次世界大战÷因能源的争夺引发的战争等等。而其他各类分配问题上产生的规模大小的战争和运动从未停止。海氏当年给出的答案是:思和诗。“做好准备,随时迎接上帝的到来和上帝的缺席。就是上帝缺席的经验也不是一无所获,而是从我在《存在与时间》中称为沉沦于在者的境界中解放出来。”这真是个一语多关的阐释。可以意会的实在很多,那就是任何绝对的进程都是尽早将人类自身推向绝灭的深渊之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突从未停止。复古要不得,彻底斩断过去,事实证明那更是无可进退。在一片断层或漂浮的空气中,存在者迟早会坠落。在这个过程中,精神日渐贫弱的国人,逐渐回首几千年的文明,我们到底需要拉回什么,放弃什么,这都是难解的问题。
书中没有长篇大论,只是客观陈列,将明逻辑或隐逻辑关系的人物和事件陈列出来,不时用时空倒置或交互的蒙太奇手法穿插牵引,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外表沉静,内里丰饶的瘫子村,是风习传说与旧规多多的瘫子村,有着万般情怀与故事的瘫子村,不能说搬就搬的瘫子村啊。另一面,政府力量的代表人物,实施搬迁计划的乡长王清举的压力和决心在更为客观的现实面前亦显得不容置疑。
但二元冲突的命题直接牵连的是与普通老百姓生息有关的问题——生活和命运的可否改善。不搬迁,就意味着踏实安全地守护老祖宗阴僻下的村庄继续与洪灾斗争,生命财产听随天命,生活照旧贫穷简单;搬迁就表明会远离洪涝,大家过上安全富裕的生活,同时也是虚空贫羸的精神生活开始,真正漂泊人生的开始。何去何从,如何取得结果,这是小说脉络走向的归结。
是的,没有一种对传统的顽抗守护最后取得胜利的。历史永远只能随着时代的洪流前进。对当下的掠夺和对过去的遗忘和抛弃,也许就是现代性的本质?小说以宿命的隐喻,戏剧性地安排一场悲剧诞生——摊子村象征祖宗魂灵存在的祠堂被烧了,代表淮河戏剧拉魂腔的灵魂人物的七巧莺死了;她的丈夫,村中最长者麻三叔死了;七巧莺的养子腊八纵火烧了祠堂失踪了;麻三叔的儿子村长梅虎为义弟腊八承担罪责,也宁愿误死在了父亲的刀下。一切精神存在的依存都消亡了,生活还要继续呀,大家只能是迈着腿向“光明”的高地行进。
四、隐藏在淮河滩上的生命深邃
流传淮河流域千年的民间戏种拉魂腔,作为当地人们心中隐约的精神背景,既然随时代的变迁沉寂多年,在现代性浪潮愈加强烈的冲击中,也不可能从故旧场景中复活繁荣了。所以,作为第二主线的拉魂腔,欲由七巧莺的间接弟子,下海经商多年的漂亮女人陶月婷主持复兴,这也必是作者暗埋的伏笔。弃戏经商的陶月婷处心积虑,把玩各种交际技巧,好容易复修好了戏台,乡长王清举也别有用心,用他煞费苦心炮制出来的剧本,即以已故拉魂腔鼻祖,在民众心中威望颇高的七巧莺的父亲为主人公,借他之名告诉瘫子村民众,只有搬迁是唯一的出路。可就在七巧莺坚定地搁置四十年的嗓音突然决定放开大唱,在长声刚刚吊起的瞬间,她的生命竟嘎然而止。这些古怪的细节不能不让人相信是一个个兀然闪现的预言。它们是有备而来的?在这样一群愚顽偏执的人物面前,他们的命运着实有些蹊跷,到此,宿命这个词就显得尤为重。这是古风颇重、阴气很深的淮河流域,其独特的神秘力量统摄下的命运必然的走向?由此联想到七巧莺对陶月婷的话:“孩子啊。到了我这年岁,还有啥事想不穿?唱和不唱不过是一种生计。早年红的时候,有多少权大利大的公子挖空心思要娶了我,我不从,他们就砸台子烧牌子。我想我活生生的人,都是别人拿来捏去的消遣物儿,何况这几句空落落轻飘飘的戏词呢?”这分明是朴素的生命哲学,出自一个七旬的老太太平静的口中,我想,这足可解释那些所谓的迷信或者怪异吧。但宏大的象征从来都是需要寻常的细节映衬和比照——天下大事,局势已定,连草芥蝼蚁都跑出来说明问题呢。
小说中体现深意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而书中的潜台词也不胜枚举。比如多次出现的蜘蛛对人世兴衰的暗示,比如麻三叔在省城的女儿梅红对家乡的特别感应,比如喜神和杀青节上的风俗描写,“我”无意间看到雪地中停在树枝上的鸟……
五、一本民俗文化小说
这部长篇将淮河民间文化展示之于小说叙事有机结合,各章节巧妙地起承转合于精致特别的结构中,以此完成核心问题和事件的延展抬升,文笔洒脱,淮河方言适当使用,让对白与描述亲疏有序地结合,读来毫无枯涩沉闷之感。加上民俗的适时介绍,拉魂腔这一戏种的有机穿插,可以说,我认为这是近年来少见的颇具浓郁民间神秘色彩和厚重文化旨归的戏剧化小说。当然称其民俗小说也许更合适。值得一提的是,每一篇开首基本以淮河风习为小引的——作者一直在以暗喻的形式,把神秘的风习铺到事件的底部,让每一个结局运行都各得其所,因果自明。
而小说的人物安排,更是没有多一个余人。每一个都跟书中的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相关联,错综而有序地交汇,让读者几乎全面地记住了他们。不论此人是学者还是农民,不论他(她)是在省城还是在瘫子村,都参与了事件和命运的延展和推进。最集中的是麻三叔这个复杂而凝聚力极强的家庭,每个人物几乎都构成了悲剧结局的产生元素。哪怕远在省城的女儿梅红,她的每一个意见都能左右父亲的意志。村中人物瞎大妈和死于火灾中的傻子,他们一样见证了这个神秘村庄的命运,他们的悲剧命运也是村庄的另一层次的缩影。最特别的是作为学者前来考察淮河民俗的“我”和我的导师姜教授。他们从旁观者的角度,现代生活的代表人物审视这个村庄,以清醒客观的视角折射一场对抗中的问题和哲学。由此不难分析在这场冲突中,他们发挥了怎样的能量。在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中,他们的存在更加深了两种文化对立的原因。
陈先发作为一位诗坛有影响的诗人,其文字虽不脱诗意气质,但该书结构严谨,层次感强,无论叙述还是对话,抑或篇幅延伸的可靠度来讲,此书作为小说的可读性毫不逊色于当红小说家。很多处对话,我是忍俊不禁了的。本书中,作者是以文化学者身份考察淮河流域的民俗和文化,了解农民的生存和现状,最后给大家奉献出这样一种文学与社会学,农民问题和传统文化如何拯救等多重内涵的叙事作品,实在是这一年对中国文坛的一份大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