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11598
- 积分
- 2259
- 威望
- 20080
- 桐币
- 927
- 激情
- 875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1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5-5-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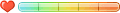
桐网嘉宾
 
- 积分
- 2259
 鲜花( 2)  鸡蛋( 0)
|

楼主 |
发表于 2005-10-14 13:11:30
|
显示全部楼层
桐城派研究的厘清与突破
■高黛英 2005-10-14 05:18:33
桐城派,又名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c、姚鼐等均系安徽桐城人,故名。
桐城派崛起于清康熙年间,衰落于民国初年,前后绵延200余年,麇集作家1200余人。它尊奉程、朱道统,继承秦汉及八家文统,创立了以“义法”说为核心的系统完整的散文理论,创作了丰富优秀的散文作品,有“天下文章出桐城”的赞誉。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实为中国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集中国古典散文、文论之大成,并占有突出正宗地位的古文流派。此派自结立门户之初便毁誉繁兴、人言言殊。进入20世纪以后,桐城派研究几经起伏。最初20年,桐城派研究是承续期,刘师培、黄侃等人批评桐城派体辞,胡适、陈独秀等人否定桐城派价值;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是桐城派研究的发展期,新文学家对桐城派不再全盘否定,而是有所选择和汲取,将桐城派作为纯然的学术对象来归纳研究,由文派流变史的研究到桐城派理论及创作的深入探讨。建国后至70年代末是20世纪桐城派研究最低落的时期,受思想文化界形而上学之风的影响,更多的论者机械运用唯物史观,从政治等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上评价桐城派,否定意见仍占上风。80年代,桐城派研究进入复兴与繁荣期,研究禁区被冲破。本时段研究论题围绕着整体评价、古文理论贡献、古文创作成就、文派流衍及历史经验教训的探讨与总结等几个方面,研究方法更新,视野扩大,多元格局形成,由简单的价值判断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与研究,理论探讨进入细化与深入的阶段。
首先,是寻求桐城派研究新突破的自觉意识与努力。一个是学术视野的突破和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方位的态势。学者们从地域文化、学术史、哲学、史学、教育史、文学史等各个方面探讨桐城文化,总结研究得失。作家选择上,不再集中于“桐城三祖”、“姚门四杰”,而扩及桐城后学方宗诚、戴均衡、萧穆等人,甚至牵出桐城派尚未创立之前的方维仪和姚鼐伯父、业师姚范;以往研究中较少涉及的尺牍、墓志、寿序、奏议、诗歌等题材的写作乃至传播情况,被学者们所关注;对作家创作心理的探讨,对文集版本变迁的论述和对作家交游的考述等,都丰富发展了该论题的研究。第二,研究方法的更新。在研究方法上还出现了以往研究很少使用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谈吴汝纶〈尺牍续编〉》平实准确地考述了吴汝纶《尺牍续编》的编纂情形、版本状貌、成书时间、所收信件编年及内容,以及该书特点等等,清晰地呈现了这部珍贵的传世文献的大致面貌。《论萧穆与〈徐骑省集〉》从文集刊刻缘起及校勘特色两方面探讨该书的版本价值和文献特征。《东跨日本访逸书的晚清学者——黎庶昌及其〈古逸丛书〉考论》,爬梳、钩稽史料,详述了黎庶昌搜访刊刻《古逸丛书》的经历,并以部分逸书为例,撮述流传原委、考述版本真伪,考订今人讹误,辨别异同得失,等等。研究手法的丰富多样使得一些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突破。
突出的地域性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文化态度方面,多数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一种天然的、地域上的亲和与文化上的认同;研究资源的使用方面,独特的地域资料的挖掘使用较为突出,一些具有前沿性、开拓性的选题及扎扎实实的论证,建立在独特的、不易搜寻的当地田野调查资料、族谱家谱、家族文本遗存甚至当地百姓由于某种机缘保存并捐献的珍贵文献资料之上;研究队伍方面,专职科研人员外,尚有不少非研究机构的人员,职业上具有普泛性特征,一些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家学或师承(再传)之关系。这些都体现了安徽各阶层对桐城派这一地域历史文化遗产的珍视和研究的热情。
桐城派自树帜文坛便毁誉繁兴,对其展开批评的历史亦不止百年。寻求研究的突破,笔者以为,首先应站在文学、史学的高度,对百年桐城派研究的实践和理念进行全面的清理与反思,并严格按照“历史的方式”,即将研究对象置于它存在的原生状态中,根据研究对象历史演进的实际状态及文学文本,进行宏观的把握和个案的研究。此问题,法国汉学家戴廷杰(作《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戴廷杰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近二三十年,有很多关于桐城派的文章,探讨某作家的文学思想,试图找出作家间的相互联系或影响。我觉得许多文章缺少证据,只是抽出几点或某些段落进行简单的比较,并不重视原文和引言的上下文。所谓戴名世的文学思想,多半是根据戴名世为某些时文写的序;像许多文士一样,戴名世提倡‘以古文为时文’,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戴名世在此类序中给出的所谓学做法则,实为一种极为特殊的文体练习,也即著名的八股文。戴名世在给侍郎赵士麟的信中,要求赵氏撕毁他请人代写而署戴氏的一篇序时,转引《易经》中‘君子以言有物’一句,难道也应将此作为戴名世文学思想的一部分吗?难道便可与方苞的著名‘义法’相比较,因为方苞曾提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吗?在这封信中,我怕看不出别的,只看出戴名世指责赵侍郎的妄贪虚荣。”戴廷杰还说:“戴名世是否属于桐城派是很难证明的。其实是无法证明的:怎可能证明一个作家属于他所生活的年代还不存在的一个流派呢?……我只是觉得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这几乎是年代记述的误差……”西方汉学家提出的桐城派研究中“史学意识”的缺乏,随意调遣材料和“过度阐释”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