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194
- 积分
- 7
- 威望
- 0
- 桐币
- 0
- 激情
- 11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1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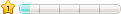
文都童生

- 积分
- 7
 鲜花( 0)  鸡蛋( 0)
|
那无疑是个不可复制的时代。当国学与西学两股巨浪在激流汹涛里进行着它们的合流时,就注定了它将成为一个大师迭出学人并起的时代。在这个合流过程中,一方面号召“整理国故”一方面又提倡“全盘西化”的胡适,也就毋庸置疑成为了这时期的一位领袖人物。也就是这个人,给中国带来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
事实上仅仅就在那个时代里,就有很多的人抱不平,对适之的思想方法给以了非常激烈的批评批判甚至是攻击。但是也正如后来人所总结的:批判适之“整理国故”者,在西学上绝少有人可以望及适之的成就;批判适之“全盘西化”者,在国学上又绝少有人可以望及适之的成就。
长期以来,教科书喜欢把鲁迅捧作那一时代的领袖魁首,适之似乎只成了一名可有可无的小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在事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在那种百家争鸣群雄并起的历史大环境下,我们仅仅做一个设想,以鲁迅之才力学力资力,又是何德何能信服众人坐上领袖的交椅?所以,领袖的位置只有适之方可担当得起,而鲁迅却不过是一条边线上的急先锋,充当着一个鼓手与战士的角色。用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刻意来回贬鲁迅,我自认为是一条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是针对于鲁迅在新文化上的建树与影响得来的。无法否认鲁迅在魏晋玄学上的成就与地位,但是他的学问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翻引者多而自身建立者寡。至于白话文上,从文学史上客观角度,中国人第一个写作白话人小说的,也并不是鲁迅而是胡适的一位留学在外红颜知己——陈衡哲。
然而世间人评世间事的时候,多数是不客观甚至是片面、偏激的。我们长期浸淫在一种标本型大师的身影之后,却往往忘记了什么才算是大师。从今天的选择角度看来,往往一味钻进故字堆,一副酸朽气的,才更容易契合世人心目中的“大师”形象了。章太炎是,黄季刚是,那么胡适之算不算是呢?人们纷纷把一个个所谓的“家”扣在适之的头上,但绝少有人谈到“大师”的时候第一直觉就可以把适之算上。因为什么?一个感觉,一个抹不掉的阴影:因为一个“新文化”,既然是“新”的文化,哪里能和这些旧文化中的“大师”相提并论呢?这世界上,又究竟还有多少人,知道适之的一生,做了多少开山式的成就?
胡适显然不是一个家学深厚的传统中国文人,而且年轻即留洋入美,在那里一口气又接受杜威式西方哲学的熏陶。所以适之的一生,几乎都不曾来得及对国故里的传统小学内容做出深入的研究。事实上,即使是对于西学他都没来得及全面而深入去了解,在这样的时候他就草草收拾行囊,赶回国内领导新文化运动,而且来到北大教书,还渐渐做成文学院长了。他最终成就文化史上不可磨灭不可替之的巨人,也许这有些像我们经常读到的武侠小说里的情节:某个原本初识武功的毛头小子,机缘巧合遇到一位世外高人传授某件武艺,从此领袖群伦笑傲江湖,而且最后还因为自己到处涉猎杂七杂八的武学典籍终于集大成了。但是,适之终究是集大成了,这是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
也许是文人相侵,也许是打骨子里就瞧不志这种烂家底的胡适,黄季刚就不知多少次当众奚落甚至恶谤适之。就像有一次聚餐的时候,黄季刚嘲弄胡适的“新文化”,就说胡先生你要真提倡新文化,就甭叫什么“胡适”了,你得改名叫“往哪里去”,这才是大白话么,哪里又“胡”又“适”的呢。结果胡适沉默不语。
胡适为什么不反击,我想至少有三层原因:第一,他性格里本身就温雅平淡,犯不着为这件事去扫落自己原有的风度;第二,他也是个聪明人,他明知在小学训诂上的功底,还万万不能跟眼前这位太炎之首席大弟子相提并论的,以己之短攻彼之长,智者所不为;第三,他自己也知道,像这些根深蒂固的旧学人物,他不可能说服他们放掉自己的老家本来倒戈参加什么新文化了,何况黄季刚这里的奚落嘲弄,几乎没有逻辑性可言,这关一个姓名什么事呢?所以,他干脆沉默,得过且过了。
然而适之就是适之。他早已经扼住了时代的命喉。新文化终于不断建立起来了,那些旧学的东西,永远挡不住新文化的黎明的曙光。不计一时之口角胜负,适之已经赢得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这些,是黄季刚永远收获不到的了。也难怪,黄季刚一次次对胡适变本加厉,甚至借假设例证在适之新婚的时候去咒他妻子死,又或者借着酒劲骂适之和其父都是混账王八。从这些故事里我们固然知道黄季刚是一种狂狷不羁恃才傲物,那么适之呢?更多的是一种儒者的内敛淡泊。
并不是抱着成堆成堆的书卷,就可以成为学者,成就大师。事实上从基础上看,必须客观地承认,适之最初的读书是很有限的。尤其对于那些古书,他当时肯定不及太炎,也许不及黄季刚、刘申叔,甚至还不及其时仅为北大学子的傅斯年。刚刚27岁的胡适之留学归来就被蔡元培聘到北大哲学门当教授,在课堂上不被这些天之骄子们信服。于是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就请来自己在国文门的至交好友傅斯年,让他来旁听适之的授课。傅斯年在听完课后给学生们这样的交待: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傅斯年的这番话,其实正好也道出了适之最终能在学术上集大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在于他幼时的基础有多深厚扎实,而在于他治学的方法是科学合理的。他从恩师杜威那里学到的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实验主义的治学思想,并被他在以后的学术生涯里得到了极好的发扬光大。他开始去涉足越来越多的领域,又恰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严谨的治学风骨,一次次取得了划时代的开山巨功。他在那个时代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恰似于当年亚里士多德之于西方,孔丘之于先秦。而这一次听课,给适之带来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财富就是:一个正欲满心扑在旧学上的傅斯年,却从此之后一步步走向了新学的轨迹。这便是适之一种超乎常人的人格魅力与学问魅力吧。
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适之的成就,除了他科学的治学思想与治学方法,与他自身并没有像腐儒一般在中国旧文化里浸淫太深,也是息息相关的。正是缺少这种过多繁冗的浸淫,使他可以借助西方的哲学思考,来从客观的角度审看中国的旧文化、旧哲学。这种思想动机,不想产生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影响到他对整个中国旧的文化体式的批判。在他的晚年谈话录里,他就不止一次向身边的后生说起古文,他的批评直入刀骨,他说中国的那些古文章大多都是不通的。恰恰是看到这一处,才使我对他有了更深的钦佩与拜服。而这种进步决然的思想认识,却不是一个常人可以拥有的,只能是胡适拥有。如果他自小就积淀了太多的旧文化基因,他可以有这种的“逆反”的精神吗?不会有。但正是这样,他才更客观地看待了世界看待了历史,他清醒意识到中国的旧文化里有太多不能效仿不能循蹈的东西。所以,新文化就应劫而生了。站在一个后来人的角度去思想,中国的文化基础,建立在象形汉字之上,而象形字从科学的意义上必然逊色于符号文字——虽然,象形文字更具备了艺术的意义。所以,由汉字形成的古文章以及古文化,都必然有不可否认的破绽,甚至有一种必须割断的毒瘤。恰恰是胡适,这个尚未全面陷入旧文化而又及时接受了新思想的年轻学者,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由此改良了整个社会。
现在回想,在那个时代里,站上大学讲堂是极不容易的。作一个简单的设想,在北大的课堂上,你会遇到诸如傅斯年、顾颉刚这一批即将领导一个学术领域的不世出的门生,而在清华,你还要面对钱钟书。所幸的是,北大在蔡元培的治理下,集中了一批如胡适之、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黄季刚这样的文化巨人;而清华也有它声名卓著的四大国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你若要问为什么,那么,唯一可以回答的,那就是一个盛产大师与学者的时代。而这些,在以后的岁月里,都已经不可复制。
胡适的思想,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这也决定着他往往两头不讨好,尤其他不会得到那些革命者们的鼓吹。然而历史的经验往往告诉我们:改良比革命更有利于历史之真正进程。我们只需要比较英伦与法兰西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上的差异,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了。革命是冲动的,冲动的后果往往是以偏激的思想,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胡适恰恰是大洪流时代一个难得的思想上的清醒者,但恰恰是这份清醒,使他往往做出一些令时人不能理解的事情。比如说,梅兰芳出国演出京剧,一群文人在那里谩骂,独有胡适去送行了,还合影了。大家都不能理解了,在今人眼里,大家都相信梅兰芳此举是为弘扬国粹了,可是在当时呢?京剧是旧文化的典型,一个新文化的领袖去替旧文化送行,这算是什么事?新文化的战士们,对他们的这位领袖几乎是动摇了,犹豫了,他们无法理解这种行为。而胡适不然,他支持了梅兰芳的此行,还不止一次告诉梅兰芳,希望他将京剧艺术融入时代的新因素。这一提议,恰恰成就了梅兰芳以后在京剧艺术发展上更大的成功,当然,也成就了京剧本身。此事而外,胡适还曾接受溥仪皇帝的“召见”,在面对的过程中甚至直呼“皇上”,又在北京城内外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革命是敏感的,只有适之可以如斯冷静,如斯智慧。
这是有生命痕迹来印证的:在那个革命与立新的风暴席卷整个中国时,包办婚姻首当其冲将被要求破产。三个中国文化界的男人:胡适、徐志摩、鲁迅,都是深身包办婚姻的危害,而这三人,都先后有了自己感情之真正归属。适之在美国即与韦莲司建立了超越友谊的真情;他的追随者陈衡哲,也一度痴情于他;即使回国之外还有一位表妹曹佩声与他情投意合。他想过离婚,也尝试过,但最终为了朱安,他最终放弃了,放弃了改变自己在婚姻家庭中最大的最真的也最人权的自由。志摩的故事早已经家喻户晓了,在刚刚遇见林徽因时,便已经决然抛下了张幼仪与刚刚出生的幼子彼得。幸好,志摩是一位思想极度解放的人,张幼仪经历过西方思想的洗礼之后,徐志摩又与张幼仪在爱情之外,建立了一种还算不错的朋友情谊。而鲁迅,这位永远不知疲倦的斗士,就只生生丢下朱安,由着她孤独终老了。
环境也是不可复制的。只是在革命的喧嚣中,又有多少人为自己革命的时候还在想过革命背后的淋漓与沉痛?狄更斯一定想到了,所以有了《双城记》;适之也想到了,所以他维持着自己的婚姻与家庭。他的选择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人格魅力:那位远隔大洋的美国情人韦莲司,就为他终身未嫁;而他那位情深意重的表妹曹佩声,直到临死前还叮嘱要将自己埋葬在胡适返往老家的那条必经的道路上:只要他还能回来,她必能第一个守到他。
不错,时代需要鲁迅,需要他用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将黑暗的夜空打破得支离破碎。但是别忘了,时代也需要胡适,默默走到革命的身后,用他一惯的温和去抚平刀与火的伤痛。假如伤痛只是继续着伤痛,也许革命纵然成功,也只不过为历史带来了又一个法兰西,让以后更为混乱的岁月为这份革命买单!
在学问上,适之是严肃的,所以他可以开辟一个学术的崭新时代,他的学术思想翻新了那个时代延伸到这个时代甚至还要影响到下一个时代;在生活中,适之是温和的,所以他可以集中很多性格各不相同的朋友,成为他们之间共推的老大哥;而在性情上,他依然是那么真实那么一如常人,所以他是平凡的,因为平凡而令人亲近着。
适之对自己弟子的维护,是人所共知的。还在北大时期,一个年轻人周汝昌为新红学写信给周汝昌,在言词里批评适之的弟子俞平伯,认为平伯的红学研究已经背离了适之的考证作风,表示不屑一顾;胡适就颇为严肃地回了一封信,叫汝昌踏实做好自己的学问。事实上,平伯的文学考证确实与胡适一惯偏爱的史学考证并不同道,所以在早期胡适最钟爱的弟子也恰是顾颉刚。然而,学生终究是自己的,他容不得别人对平伯的治学有任何说三道四,这就是一个性情中的胡适之。以后大陆掀起了针对胡适的大批判,平伯因是适之弟子必然遭到株连,蒙受太多不白之冤。隔海相望的胡适已然老矣,但是在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他仍然震怒了。事隔多年以后,当他重新回顾起自己的得意弟子时,已经开始将颉刚与平伯并起。也许只有他自己才能深深明白,有一种怜爱竟如这般伟大而平静。
除了维护弟子,适之也习惯去维护自己的安徽老乡,成为极耐人寻味的一道风景。比如他不止一次在立场上为李鸿章作积极辩护。除此而外,他晚年倾力考证《水经注》,最原本的动机竟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另一位清朝同乡——戴东原。他不止写出了《戴东原的哲学》,甚至在《水经注》的上研究深度,至少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了。
适之是很真实的。任何一个真实的人都必然有自己的愿想,有自己的私心。他维护自己的弟子,维护自己的同乡,都是源于一种私心的真实反映。舍此而外,他这个北大校长的位置,也是因为自己的得意门生——傅斯年主动成全的。最初接到北大校长这一职位聘请的,恰恰是傅斯年。不过傅斯年知道,胡适一直有个极大的愿望,是可以自己出任一次这座著名学府的校长。于是,傅斯年成全了胡适,一如当年在北大哲学课堂上那一场暗中的维护。或许,这就是种善因得善果吧。成全别人的,终也会得到别人的成全;维护别人的,终也会得到别人的维护。适之,就有这样不可替之的魅力。
于是我无数次走进了这位圣人的世界,在我眼里只有平凡的才是圣哲的,适之正是这样一个圣人。恰恰又是在这种际遇下,我竟然看到了另一个熟悉的身影:徐志摩。
志摩不同于我一向热衷的三位文化大贤:方密之、梁任公,胡适之。他是另一种形态的存在,他是诗人。当然诗人在我们今天,有可能是除了写诗,就什么都不会了。但那个时代不同,那是个群英璀璨的时代,而志摩必然是那个时代的先知与先行者。因为,他是诗人,而且是一个纯的诗人。
什么是诗人?春江水暖鸭先知。诗人所具备的独特而敏锐的气质,使他天生就能比常人更先闻到时代大潮将来的讯号。于是,新月派应运而生了,在这里,有他,有适之,还有很多很多的战友。而志摩,便是最典型的一位新月人。他轻轻的来了。他来得似汹涌又似安宁,但至少,他来得很纯,不带有一丝的酒精气。在中国的古代,诗人往往与酒精是紧紧关联的;所以中国的旧诗,虽然逃不出格律的方框,却在行文与表达中多多少少透着浓厚的酒精气。志摩却没有,他就像自己时常戴着的那架金边眼镜,安静得就如民国时期典型的留学生。那时期的留学生所独有的气质,从他的诗行里不由自主又毫不带杂质地喷薄而发了。
他的性格大不同于胡适,但他却与胡适结成了最亲近的朋友。从另一个看角上讲,胡适也俨然成了他生命里的老大哥。志摩是天真浪漫的,因为天真浪漫他有时就像一个孩子,在繁华的世界里到处奔跑着,甚至是闯祸着,例如陆小曼事件。仅仅是这件事,胡适就辛了大苦。他既然劝不动让自己这位弟弟收手,又只好在一旁暗暗地周旋着、维护着。于是,王庚和陆小曼终于“和平演变”了,而胡适却摇身一变成了徐、陆婚礼的主持。单单是这一件事,胡适甚至被志摩的恩师、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梁启超一顿责罚。用后人旁观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场感情风波的故事,何尝不像是调皮的弟弟在外面闯了大祸,而老实厚道的大哥哥却跟在后面收摊子?虽然称不上喜剧,但多少又传达着一种友情的温馨。这件事的续集,定格在志摩死难之后的著名“八宝箱事件”,志摩这个做弟弟的真不叫人省心,即使自己惨遭横死,依然留下了一地凌乱的旧帐,留给这位可亲可近的哥哥来帮忙收尾了。
我时常觉得,判断一个男人若何,也许看他身边的女人,可以作为一个侧面的支撑。当然,这一定不能包括包办婚姻下的建立关系的女人。我们回过身看志摩身边经历过的女人,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韩湘眉,等等;再看胡适之身边经历过的女人,韦莲司、陈衡哲、曹佩声,等等;最后还可以比较一下鲁迅身边经历过的女人,许广平。好像不需要再多说什么,就已经泾渭分明了。当然,我不否认,在比较这三个人的时候,我不由自主也带入了自己的主观感情,因为我不是机器人,就不可能不带有这份主观感想的。
并不是因为走进了胡适所以走进了徐志摩,却在分别走进的两条道路了,找到了一个超乎意外的惊喜。恰是这种惊喜,使我对适之与志摩,又平白多添了几份纯感性的喜爱,纯感性的坚诚。
似乎在提笔之前,我脑海里还翻涌着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想在文字里一一说清。但现在看来,未免太过没完没了。那么,把剩下的留给日后可能会有的续集吧。以此献给我所敬爱的适之先生,以此祝福我不可能再相遇的志摩,以此缅怀那个绚烂而不可复制的时代。
(2011/1/17,凌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