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100454
- 积分
- 156
- 威望
- 51
- 桐币
- 345
- 激情
- 329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112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13-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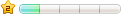
文都秀才

- 积分
- 156
 鲜花( 2)  鸡蛋( 0)
|
六尺巷
中国有一条巷,说它短,还真的短,只有一百五十米;
中国有一条巷,说它长,还真的长。《礼记》里面有一个“礼”字,《论语》的“温、良、恭、俭、让”里面有一个“让”字。这样说来,这条巷至少有几千年的长度。
“礼让”这两个字经圣人这么一点,历朝历代的贤者哲人手中拿着一把铁锹,不断的挖呀掘呀,虽然发掘出一眼眼清泉,却也垒了一堆堆文字的山,遮挡了人们的视线,将简单的两个字掘得纷繁复杂,深奥难懂。站在今天的巷口,才领悟到这两个字的真实内涵。其实“礼让”不是意思上的难懂,而是行动上的难为。
把墙基往后挪三尺,让一面墙成为镜子,照出自己的透彻,照出自己的不争,也照出对门的愧疚。于是另一面的墙基也往后挪动三尺,人心就从争执中脱变为礼让。“一纸修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站在石刻前,我默诵的不仅是一首诗,更是一种胸襟,一种胸怀。讲解员说:张英是低调的。其实,低调的不争正是高调的宣扬,宣扬两个字——礼让。
中国有一条巷,说它窄,还真的窄,只有六尺。窄的容不下纷争,容不下仇视。
中国有一条巷,说它宽,还真的宽,宽得如海,将波涛一一容纳;宽得如地,载得大树小草。走在这条巷,我思量它的宽度,这是实实在在的六尺,我甚至用我的脚步度量过,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这是一个人胸怀的宽度。一个人的胸怀有多宽,一句广告词说的好,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宽度,有怎样的民族文化,就会蕴藉怎样的人文胸怀,五千年厚重的中华文化,蕴育这懿德流芳的六尺巷。
为什么我们要提倡和谐社会?难道“和谐社会”的精髓不是礼让?睁眼看看:官场为了权位尔虞我诈;商场上为了金钱你欺我骗;职场上为了晋级你争我抢。就让这些人走进这六尺小巷,在两边如镜的围墙上照照自己龌龊的灵魂,让一首诗成为一条鞭子,拷问灵魂,让淳朴的古风沐浴灵魂。
中国有一条巷,叫六尺巷,在桐城。我来时,正值农历八月。我轻轻地走过,两边院墙内正丹桂飘香。
文庙
在这里,我仿佛看到一个耆儒站在一片空地上,捻着几茎胡须,心里计算着一种高度,一种仰止的高度。然后把这种高度画在一张纸上。
在这里,我仿佛看见一群工匠在那片空地上挖地基,地基很深也很宽,因为只有地基挖深挖宽才能承受那种高度。然后一群工匠一块砖一块砖地垒砌心中的高度。一片瓦一片瓦地盖好,呵护心中的这种高度。
在这里,我仿佛看见另一群能工巧匠将铜块塞进一个大炉子里,然后拉起风箱吧嗒吧嗒地诉说,将铜熔化倒进一个“万世师表”的范式中,铸就自己心中的偶像,一种高度,令人仰止的高度。“四配”、“十二哲”也一一铸就。
这一天,一座建筑盖好。一种仰止的高度落地生根。于是,那位捻须的老者领着一群儒冠博带,把早已请人题写的鎏金匾额一一放在恰当的位置,一块是“圣集大成”,一块是“与天地参”,“大成殿”是其主体建筑,举架高昂,面积广阔。气势恢宏,巍峨壮观。最后一块“文庙”嵌好,只待特定的日子到来。
这一天,一个特定的日子,九月二十八日,圣人的诞辰。这一天,秋高气爽,风霜高洁。这一天,炮竹声声,锣鼓喧喧。这一天,万人空巷,络绎不绝。文庙广场,香烟袅袅,人头攒动。文臣鸿儒,纷至沓来,缨带飘飘。一个声音喊道:时辰已到,祭祀开始。三牲呈上供桌;斟酒;圣像巡礼,四配十二哲巡礼;圣像归位,四配十二哲归位;众人跪拜。这一天,我是万人从中的一个秀才,我亲历了那场洗礼。
这一年是元延祐初年,公元1314年。据说:这一天下午,还下了一场雨,人们都说,那是圣人惠及万众的甘霖。于是明清以降,出现了堪称“十七世纪罕无伦比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方以智;出现了以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雄霸文坛200余年,是中国文学史上迄今为止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这一切,与一场雨有关。
今天,我以一个等同于秀才的教师身份来拜谒。未进广场,我将心灵打扫,我不得不承认,在当今社会,我的灵魂蒙尘了,我只有打扫干净才能走进您,才能让您的灵光把我的灵魂照亮。站在泮桥上,我是多么轻易就踏上泮桥。而古代多少读书人皓首穷经,兀兀穷年,想通过这座桥去拜谒去朝圣而不可得,不得不望桥兴叹。因为只有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能踏上泮桥。说实话,我很少跪神跪鬼跪佛爷,但面对“万世师表”,我跪下自己的灵魂,我毫不怀疑自己跪拜的虔诚。我跪下,您是一座山的高度,一种仰止的高度。我愿意把这块匾挂在自己的心壁上,做灯。
据说:有人动议,从明年起将教师节移到九月二十八,如果进行投票,我举双手赞成。
孔城老街
有一种宁静蕴繁华,如大音稀声。有一种漫步是穿越,如我此时的闲散。
此时,我正漫步在桐城的孔城老街上。一条长达2.2公里的“S”形街道,足够让我与它来一次亲密接触。不去追溯它有多少年历史,不去数它有多少条小巷,多少里弄,也不去计算古建筑有多少幢,临街商铺多少间。用脚步去叩响每一块麻石条,用手去触摸每一块青砖,每一块小瓦。其实叩响的是历史的回音,触摸的是历史的脉搏,寻找的是早已遗落在繁华外或温馨或酸楚的旧梦。
伫立桐乡书院,一千多年前的琅琅书声在书院上空回荡,久久不散。捻胡须的老先生诵读着关关雎鸠,读到沉醉时闭上眼睛把头拗过去,拗过去。一个个学子走在通往乡试、会试以及殿试的路上。一张黄榜之前簇拥着数以万计的头颅,一报、二报、三报的小黄旗在孔城老街上飘扬,捷报频传,绵延千年。
徘徊在石条道上,八百年前的吆喝依然响亮,各种方言在这里撞击。茶馆内有闲阶层坐下,来一杯碧螺春或一碗盖碗茶,茶碗里散发着地地道道的方言味道。铁匠铺内是叮叮当当的声音,押的是平水韵,平平仄仄。货栈内,码头上,车马云集,悬帆片片,账房先生的算盘拨得噼里啪啦,烟斗上烟灰明明灭灭,脸上的微笑生动而绝不僵硬。
踟蹰于白果厅遗址,一百五十年前矗立的两棵白果树蓊郁茂盛,荫庇后人。不幸的一场大火让生命成为朽木,遗留的残骸至今让人触目惊心。李鸿章钱庄,那成色十足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依然还会灼痛人的双眼,倪府的红灯笼还是那么红,只是官府差役变成了今天的来自东西南北的有客,进进出出,红红火火,一样不减当年的旺盛。
逡巡于语录墙前,一行行标语已经黯淡了从前的光芒,让人看到流走的岁月,世事的沧桑,醒着一种痛苦的记忆。邮电局内,我仿佛看到自己三十年前的身影,举着一封信件投向邮筒,或者拿着一张稿费汇款单脸上灿烂如花。电影院的售票窗口,我拿着一块钱买的两张电影票,高兴地向女朋友挥挥手,一块钱成全了一次浪漫旅行。
走到另一个出口,两公里的路程,一段浓缩的历史,在不知不觉中读完,我愿把这段路重新走一遍。于是我再一次叩响每一块麻石条,触摸每一块青砖小瓦。岁月如流水,老墙斑驳,瓦楞沧桑,雕花木格窗的风雨,石条却被打磨得锃亮光滑,一一镌刻者岁月的痕迹,是水去岸留痕啊。
岁月如流水,流去了许多许多,往日的喧嚣与繁华,一茬又一茬的苍生黎民,一曲又一曲的悲欢离合。但流不去是一代又一代叩响麻石条的橐橐跫音。 |
评分
-
查看全部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