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93376
- 积分
- 90
- 威望
- 0
- 桐币
- 10
- 激情
- 151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54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13-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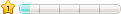
文都童生

- 积分
- 90
 鲜花( 0)  鸡蛋( 0)
|
 发表于 2013-3-2 04:41:45
|
显示全部楼层
发表于 2013-3-2 04:41:45
|
显示全部楼层
【101】
母与子
(2013-03-02凌晨1点半-4点绥化)
1.
老了,母亲,一生劳累累积的病,一下子爆发出来,于是,年迈的母亲,多病。其实,多病的母亲,中年以后就多病,老来尤甚。我念书的时候,母亲正是我的年纪,三四十岁,她健壮但劳累过度,坐下了病根,一辈子都遭受折磨。俗话说,干活累不坏人,但用力过度总不免内伤,内伤最难医治。医生说吃西药没用,还不是手术所能奏效的,需要养。劳苦了一辈子,花甲之年才记起“养”,似乎是天方夜谭。
前几年,大概2010年春,母亲胃溃疡,胃出血,疼的满地打滚,在山西长治北家里,那个晚上,是二弟连夜把母亲雇车拉到长北医院,做了胃镜,住了四天院,花了两千多块,就回家吃点小药,“疗养”了——其实也闲不住的,找了些活,在附近打工,挣得虽不多,可也够父母吃粮买米的。经常,母亲也出去拾破烂,走路,路边有矿泉水瓶,哪怕一个离着老远,母亲也过去捡起来,回家攒着,积攒多了卖掉,她说日子是攒出来的。在绥化这一年,母亲也是,似乎一些老年人都喜欢拾破烂,他们很信奉节俭的教条主义,这正是传统意识的美德。
母亲讳疾忌医,有病只好拖着,拖来拖去,拖大发了,拖成了病灶。其实,母亲不是不想看病,只是舍不得钱而已,母亲是从苦时候熬过来的,自然知道自己没大本事,小钱难挣,大钱挣不来,所以,母亲一样的人,都这样庸碌过着草根一样的生活。草根很羸弱,自己受了委屈和欺负,还是坚韧的生长着。母亲也是,她一辈子不晓得受了多大委屈,都吞下去,不与人说,偶尔她自言自语,只咕噜几句了事。或因父亲的责备,或是儿子们念书伸着巴掌朝她要钱,或者日子实在困难大劲了,干脆,她就一转身,躲一边自己哭。满世界的女人好找,但能真心与我瘫痪的父亲过日子的,怕惟有母亲了。母亲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她的故事并非三言两语,敲了若干次回车键所能讲完的。我语重心长的母亲。
2.
下时候,都说父亲是拉车的牛,我看母亲更像一块土地,默默承受着一切不幸。每当开学,我在县城念书,要坐老远的乡下的线车到绥化去,等车地点就在俺小屯子东头,砂石公路一拐弯的地方,从东而来的砂石路向南怪了个斗弯,90度的斗弯。冬天的砂石路积满了冰雪,巴掌厚的瓷实的白雪,一场场雪一层层碾压上去的,路面很滑,车子开过去,兜起一阵旋风似的雪雾。
3月一,是开学的日子,天底下的学校都恪守着一个令,不约而同恪守着。就像屯子恪守着冬闲两顿饭、农忙三顿饭那样,很多习俗大抵就是乡规民约。那也是年后,一个冷日子,父母凑了些钱送我去念书。那时,俺家没钱只得东挪西凑,“凑”成了惯例。当凑来的钱花没了,真的没什么再值得往上凑了,只得砸锅卖铁了,我念书就那样紧巴,所以,今个我念念不忘。记得那次,天格外寒冷,母亲给我拿了家里尽可能的嚼馃,告诉我到学校里吃。那是个没有站台的小站,露着天,大概中国乡下所有的候车点都那样,既没什么站牌,也没站务管理员,只有村庄屋舍道路。冻死人的冷天,等车的竟不少,我是一个,那时,我真天真,孩子似的,只知道念书出人头地,决心倒是不小,可期望值一波三折。原来,奋斗的路那么九曲回肠。
开学了,母亲送走了我,送着全家的希望。也许,母亲多想送走寒雪堆砌的冬天,让雪花携着老北风回到春天的墙外,让清贫的日子生根开花。也许,母亲多想有一座2月末的小桥,把2月慢慢过渡到3月的初端。可是,3月一,来的那样突兀。就这样,3月飞快的立在了眼跟前儿。上学的走了,母亲也开始了备春耕,一大笔天文数字刚刚被我支走,又要买种子化肥。
那时,豆种自家备份的,是前一年割豆子时,看自家豆地里那块豆子长得好,就顺便留出来做豆籽。很简单,从豆子植株颜色即可判断的,那种老褐色略微黑红的豆秧,即可,籽粒粒粒饱满,每一个虫眼,有虫眼的豆籽做不成的,农事里针鼻大的纰漏都马虎不得,疏忽了,好像总对庄稼不放心,怕粮食打不不出产量似的。每年秋,豆籽提另隔出来,打场时也格另打,之后,也得挑选一遍。那时,个人家哪来的选种器,选豆子就能手工,用饭桌子——方木炕桌,在火炕上支个斜坡,用筷子阻隔住豆粒旁逸,用筷子和手指拨啦,把砸碎和碎豆瓣子剔出去。寒假了,年过了,开学之前,正月里,一家人挑豆籽是最大的活。我也帮母亲挑豆籽,从早熬到下晚,掌灯了,还在挑,一连三四天才挑完。手工的活,格外不含糊,可谓精细百倍了。
时光总象一个幽默的故事,虚晃一下子溜走了,然后,跑到你前头。幽默长在生活里。腊月正月却从不幽默,它们冷的铁面无私,阴沉着脸,呜呜的吹着北风。我则尽日不出屋,甚至不下炕,享受着火炕的暖滋味。是啊,火炕暖的滋润,如若再做一份鸡蛋糕子,找个小匙吃掉,继续赖在热炕头听收音机。每天晌午,听评书是我最大的爱好。寒假里有评书听,真幸福,我一辈子没进过茶社书馆,现在也没说书讲古的地方了。母亲则喜欢听豫剧,每收到豫剧的波段,就紧忙招呼母亲,母亲正在外屋忙着。小花猫小花狗不停地叫着,棚顶裱糊的报纸昆黄,是岁月的底色。母亲听着戏,冬日的时光那样悠长,一如鸡蛋羹清香得悠长回味。那时,乡下没得酸奶,只有土生土长的笨鸡蛋。笨鸡蛋原汁原味,可也舍不得吃,一个一个的攒着,给儿女们攒着,卖了钱,用处大着呢。
儿行千里母担忧,孩子是母亲一生的牵挂。多年前,很多次了,母亲为我装包提包,母亲送我去念书,去县城。每次远行,都提前下了场大雪,大雪好大,落地有声的沙沙着,午后又是一轮太阳高挂。地老天荒的冬天,地老天荒的寒假。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也许,母亲心里,孩子永远长不大,母亲眼里,孩子百看不厌。当然了,母亲还是不厌其烦的唠叨,在等车的那短短的空档里,一句话往往嘱咐三四遍,什么早饭一定要吃啦,吃饱喽,冻着感冒了要吃药打针。是啊,母亲,没完没了地絮叨。絮叨是无微不至的关爱。孩子总有一颗敏感的心,感悟幸福。
那是个冰雪的小站,从村庄到城市的小站,数九寒天,人世间的故事也在那流转着。过年期间,车次从年三十停到初二,初三老早的发出新年首班车。烟花炮竹响尽,渐稀渐远。寒假,寒年,寒冷的日子里,人们在火车汽车里拥挤不堪。乡下客车也有春运期的,还有插秧割稻的季节,外出打工的多,车子也相当拥挤。开学之前,俺那穷乡僻壤求学的没得几个,车子挤,自然是外出打工的多,到县城办事的多。小站算得个长途汽车站了,从俺那直接开往市区中心的鑫淼城。每次开学,我背着个鼓鼓的书包,还有拆洗一新的行李。寒假里母亲拆洗得干干净净,那行李,还散着悠悠的肥皂香味。最怕这样的离别,最终,却不得不离开。求学的孩子们不都这样,每年一度候鸟式的大迁徙,春节返乡式的大迁徙。
吃不够母亲做的土豆白菜,听不够母亲问长问短,待不够自家自由自在的老火炕。在家千般好,出门世事难。谁家没难唱的曲,谁家没难念的经,穷人家孩子念书一个字苦。在我意识里,每次开学便是母亲最犯愁的时候,那时,农家都靠那点可怜的粮食过活,靠天吃饭,巴掌大的责任田能产几个大子。俺家叫我折腾的镚子皆无,父亲的腿病疼得翻来覆去,连一片止疼片都舍不得买,唉,一分钱憋倒英雄汉。俺家的苦日子竟过到一分钱都没有,确也坚持着熬了过来,母亲父亲相依为命。今天,我躲在光明中默默观看,追述那些过往的影子,我跟个事主似的,禁不住唉声叹气。感喟曾经!自己曾经那么悲凉热烈。
每次,母亲给我拿钱,递到我手里,总不吭声,也不挪步,静默一小会。虽然母亲还那样平静,脸上不表现出来,可我知道母亲心绪沉重。记得每次临走时,母亲从木柜子一角,把纸包纸裹的一小卷钱,很少的几张纸币,用针线缝在我衣裳里,那细密的针脚叫我想到孟郊的诗句,“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不单单是我,二弟三弟每次出远门,也是,母亲把皱巴巴的钱缝起来,缝的结实牢靠,生怕丢了。缝钱成了母亲的习惯,大概中国女人都这样教育他们儿女,中国人出门都这样藏钱。那些平淡的细节,是这世上最真最深的感情。
那钱,是母亲费尽了周章暂借来的,好话说了一大车,从好心人家临时借的。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借了,就要遵守诺言,母亲作zuo多大的难,也想办法堵上那窟窿。母亲要得就是个骨气。母亲的心,真够苦的。今天,忽然提起这些,我总忍不住咧嘴欲哭,但噘起抿紧了不哭,其实,眼睛早已湿湿的了。我把自己的往事看在眼里,不由自主的写下来,心隐隐的地揪着感触。那些逝去的淡淡时光,浓烈的亲情,丝毫不煽情,也不矫饰。真情实感面前,多么敦厚的铁骨硬汉,都有一颗天性的脆弱的心。亲情无价,亲情是人性骨子里的本能。
(注解:此文第二大部分,首先借鉴了辽沈女作家陈子华的诗歌《2月28日,开学了》。其次,借鉴了桐城网桐油——淡苒2013-2-26的散文《母与子》。还借鉴了桐友跟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