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ID
- 31724
- 积分
- 122
- 威望
- 56
- 桐币
- 63
- 激情
- 251
- 金币
- 0
- 在线时间
- 19 小时
- 注册时间
- 200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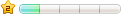
文都秀才

- 积分
- 122
 鲜花( 0)  鸡蛋( 0)
|

楼主 |
发表于 2011-8-5 23:41:45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爱塔谋叛
爱塔,原名刘兴祚,初因违犯明国法令,开原道将予以杖责,兴祚又怒又惧,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离开父母妻子,逃人建州,努尔哈赤甚喜,“授以备御之职”,改名爱塔。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进驻辽东后,爱塔驻防金州,升为游击,六月进为参将,八月升副将,管辖金州、复州、盖州、海州四州。其侄为海州参将,弟为游击,在当时的汉官中,可以说是官运亨通的名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刘兴祚竭力为金国汗、贝勒服务,追捕逃人,胁迫避居海岛的辽民降顺,击杀明朝官兵。《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二十三,载录了刘兴祚的投金及其在天命六年四至六月立功升官的情形,现摘录如下:
乙已年(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太平之时,爱塔弃其父母妻子故乡,来归于汗,汗惠爱之,授以备御之职。得辽东后,给与游击之职,遣官金州。到金州城,见城内惟有书生二人、光棍十余人。次日询之,回报皆已避遁入海,乃遣十余人,分二路把守海岸通道。夜间,有二船来此岸取粮,捕十五人,夺其船。得此船后,致书各岛劝降,十五岛之民尽数归降。
此后,四月十六日,闻登州之人驾船三十四只渡海,来金州,遂连夜往迎,遇敌交锋,射死四人,擒二十七人而回。海内七十里外,有一广鹿岛,杀我方遣去招降之一人,捕一人解送山东,乃乘船前往,擒何游击,获二千余人,以及金一百两、银一千三百两,拾刻褂皮钝子、衣服、绸帛共三百件,送来。
又,登州之兵,驾船七十五只来攻,我往战之,射毙七人。其兵败退,爱塔率一百五十人,乘船往追,不及而返。又,明国翰林院给事中等官,赛赐朝鲜国王衣服,朝鲜之二总兵官、一侍郎送彼归国,乘船二十只行于海,因未得顺风,漂至金州岸边海岛。六月初七日闻讯,爱塔率三十人往,其众官员登舟已去,未能捕获,不及登舟之朝鲜人五十二人及明国之人九十人,悉被擒获,得银四两。
因有此功,升爱塔为参将,赐银五百两、备有鞍辔之马、甲胃、细甲叶袖、弓、撒带、箭二十支、帽、带、靴等,尽赏与之。
此后,刘兴祚继续斩杀明国来兵,搜寻明将派来的奸细,追捕逃人,为巩固金国辽南辖区,防敌,平叛,止逃,立了大功。
刘兴祚还负责催征所属兵民上交租赋。天命六年十一月,刘奉汗谕,运送盖州官中谷草于耀州,以饲养军马。十二月,又三奉汗谕,赶送盖州、复州官赋之草,运往辽阳,并速将盖州、金州、复州官赋征收押运。第二年二月,汗令刘兴祚将金州、复州、盖州、海州四卫会驾驶木船的人员,尽行查出,使运右屯卫的粮谷。又叫刘兴祚督促役夫,“要不分昼夜赶快用刀船架桥”,“要勤勉地多煮官赋之盐”。
刘兴祚的效劳,受到金国汗的嘉奖。努尔哈赤不仅一再给刘升官晋职,还常下汗谕,劝其谨慎小心,防护身体,免陷奸计。天命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努尔哈赤谕告刘兴祚之侄海州刘参将说:“尔参将和我处之人一样,河西之人将要下毒,谋害尔,尔食物之时要注意。尔要注意自己身体,多派遣可以依赖之人看守尔家之门。送信给尔叔爱塔说:食物时,要注意,多派可以信赖之人守门。”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达给刘兴祚的汗谕,对双方的关系,讲得十分清楚,摘录如下:
汗之书下于爱塔副将:汝_上之书,皆已看阅。依照旧例汗所规定征收之各项官赋,勿增勿减,照旧征收。辽东周围与女真合住地方之人,草尽粮缺,若不将女真未至地方之一谷、草征收通融,则兵马何得而食。汉官私下擅自征收之谷、草、小麦、芝麻、线麻、蓝、笔、纸等诸物,俱皆革除。为此,今后差遣官员,皆以汗之库银与之,令其持带,各自买肉肴而食之。只给以米,用以食饭。刘副将要将此谕下达及南边四卫之人,南四卫之人皆信尔之言。要善为教谕,语以更新之际,虽有所苦,然汗之政法明矣,终将得安。尔须善慎其身,勿陷当地人之奸计。
这道汗谕,讲了刘兴祚肩负催征官赋的责任,讲了汗要革除汉官勒索民人的“仁政”,而这个仁政,只有爱塔副将才能宣扬,辽民才相信。它还表明汗对刘的信赖和爱护,叮呼刘要“善慎其身”,防中奸计。进人辽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刘兴祚与金国汗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样。
虽然努尔哈赤欣赏刘兴祚的才干,依靠他来维护辽南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的统治,多次嘉奖厚赏,越级提拔,半年内由备御三次升迁,晋为副将,成为降金汉官中仅次于汗之女婿抚顺额驸李永芳、西屋里额驸佟养性的第三位高级汉官。刘兴祚在一段时间里也确实尽心效劳,在征赋、防敌、平叛、止乱、捕逃、安民等方面,为保卫汗、贝勒的江山,出了力,立了大功,双方互相依靠,各有所获,关系是密切的、融洽的。但是,历史是变化多端的,辽东地区反金斗争的惊涛巨浪,冲断了联络双方的桥梁,这个曾经效忠于金国备受汗重用的爱塔副将,经过彷徨犹豫,最后终于走上叛金归明的道路。
明人李介所著《天香阁集》的《刘爱塔小传》,对刘兴祚的反正始末,作了如下叙述:
刘爱塔,辽人也,幼俘入□,伶俐善解人意,某王绝爱之,呼为爱塔。爱塔者,爱他也。及壮,配以□□,使守复州。爱塔素有归朝意,东江总兵毛文龙使人招之,为人所告。某王发兵围复州,缚爱塔归,将杀之,□□泣请,乃免。(后卒归明)。
马晋允的《通纪辑要》,亦载有刘兴祚的事:“天启三年九月,麻羊守备张盘收复金州。先是,奴以刘兴祚守复州,兴祚欲反正,事觉,奴缚之去,尽戮金、复等处辽民,逃者甚众。”
上述二书都讲到刘“素有归朝心”,要反正归明,此说不够准确。刘兴祚原来是真心为金效劳的,但后来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逐步不满金国,有了回明的念头,并于天聪二年(1628年)潜逃入明,率军对抗金兵。为什么刘兴祚会尽改初衷,从叛明降金转化为归明抗金?显然这是与他的亲身经历和辽东人民的反金浪潮密切相关的。
刘兴祚本来是因为不满明朝官将的欺压凌辱,在即将“挞之”的威胁下,被迫抛弃父母妻子和故国家乡,从开原逃入建州的。但是,十七八年的经历,特别是天命六年三月进驻辽东以后一年多的耳闻目睹及其亲身所作所为,使他感到,此处并非天堂,八旗官将并不是为民谋利的救世主,他们一样是掠夺民脂民膏,谋己私利 ,其残酷性、野蛮性、贪婪性,比诸明朝的贪官污吏凶横悍将,有过之而无不及赋重役繁,冤狱频兴,掳掠盛行,杀声不绝,幅员辽阔的辽东地区,找不到一处安静之地,广大辽民被斩被掠被迁被徙,哭声遍野,血流成河,流离失所,惨不忍言而在这造成辽民陷入水深火热的地狱过程中,刘兴祚不仅并未置身事外,不能自夸清白,相反,他却成为金国汗的得力鹰犬,起了女真官将不能起的恶劣作用,是造成这场灾难的重要帮凶。才干出众,武艺超群,胸怀大志的刘兴祚,竟成为千人骂万人恨的民族败类,真是既可悲,又可恨,实在令人痛心。这是促使刘兴祚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叛金投明的重要因素。
天命七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也给刘兴祚以极大的刺激。这年的三月,总兵官穆哈连遣马守堡去带领筑造城池的人夫车辆和牛,此人玩忽职守,不去催促牛、车和人夫,却在村里大肆敲诈民财,勒收银两。村民向爱塔副将告状。刘兴祚将马守堡带来询问,责备马不去催促车牛人夫,却索取民银,将马逮捕。穆哈连知道后,派阿布尼送信给爱塔说:“此路系汗给与我之地方,尔为何逮捕我所派遣之人?”爱塔说:马守堡犯有勒索财物之罪,因而逮捕,须另差催促人车牛的人员。阿布尼不听,耍无赖,不住在给他找的房屋,“却执拗地住在爱塔副将之门下”。刘兴祚忍无可忍,携带穆哈连送来的文书,向法司告发。法司审问穆哈连说:“尔为何不与众人商议,倚仗大臣之势力,遣人至他地挟逼?”遂定其罪,革其总兵官,“尽夺其一满洲牛录、三千汉人、于广宁所赏之财帛及所赐之人”。
这个官司,刘兴祚虽然打赢了,但得罪了穆哈连,此人久经战阵,历任固山额真、总兵官要职,深受汗的重用,地位很高,权势很大,将来势必要找机会报仇算账。而且,一个汉官,竟然敢于顶撞上司,告女真总兵官的状,还告准了,兔死狐悲,其他女真官将对刘也不会有好感,刘兴祚为此事得罪了一批握有实权的女真高级官将,种下了祸根。金国汗的验马乌尔古岱,身任督堂、总兵官,权势赫赫,就曾公开宣称,和刘兴祚“有仇”。机智的刘兴祚,对此事的后果不会不考虑,很难安枕了。
过了两个多月,六月初七日,刘兴祚又告了一状。盖州北面30里的博罗铺,瑚什塔牛录的阿哈硕色,欺压与他合住的汉民,使用汉民的牛耕田,役使汉民干活,强迫汉民之妻煮饭,汉民养的猪,只给一二文钱,就把大猪“蛮横地捉去宰杀”。汉民向刘告状。刘兴祚遣一人送去满汉文合写的文书,宣传汗禁止女真欺压合住汉民的命令。阿哈硕色竟撕毁文书,捆绑派去之人,并蛮横地喊叫:“爱塔系何等大臣,与我合住之人,尔凭什么审断。”刘兴祚又派二人前去,差一点被对方捆绑殴打。刘兴祚向上告状。法司命将刘兴祚遣去之人执送辽东,令瑚什塔牛录之人前去擒拿阿哈硕色。
这些事实表明,哪怕刘兴祚尽心竭力为汗效劳,也不会博得八旗贵族的真正信任,更谈不上对其尽职的尊重,仍然是汗、贝勒的“外人”。虽然他已荣任副将,被汗委任主管金、复、海、盖四卫,但并没有什么实权,连一个违法虐民的女真牛录下的阿哈都管不了,如果要坚决履行职责,执行法令,依照汗谕稍微保护一下汉民的合法权益,他就会引起依仗家主权势为非作歹的恶奴及横蛮随员的反击和蔑视,遭到他们的主子—八旗女真贵族官将的压制,惹恼掌权者,碰得头破血流。这些事实深刻地教训了刘兴祚,促使他下决心脱离金国,返回明境,走上抗金之路。
辽南金州、复州、海州、盖州,邻近大海,易与明国官将联系,明东江总兵毛文龙派来的奸细活动频繁,汉民早就秘密开展了反金斗争。刘兴祚利用主管四州的职权,积极准备,待机起义,人多嘴杂,风声难免泄漏,金国汗听到毛文龙派人潜来的消息,下令清查。天命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督堂下达文书说:“据悉毛文龙遣派五十人,离间吾国”,若即擒拿送来辽阳。“若不拿送,被他人告发,则治以灭门之罪”。山由岩以南,令副将爱塔清查。第二天,金国汗又下达汗谕,责令戍守南海沿岸的统兵大臣严加搜寻。
刘兴祚置之不理,继续进行反金准备工作。不料,叛徒告密,走漏了消息。这个汉民族的败类从复州跑到辽阳告发说:复州城里的男丁,原来只有7000丁,现在增加了11000余丁,还接受了从那边(明国)来的奸细和札付。复州之人将全部叛逃。开始,汗、贝勒还半信半疑,但因事关重大,遂于天命八年五月初九日,遣大贝勒代善带兵二万,前往察看,相机处理。代善到后得知,仅仅四五个月,复州的男丁就比八年正月清查时多了11000余人,“还把所有的粮谷全部作为炒面”,“叛变之事是真的”,遂纵兵大肆屠杀,撤消了复州,分成许多地方。
刘兴祚身为掌管金州、复州、盖州、海州的主将,常在复州驻守,复州全城居民合谋叛金,欲图逃往明国,没有他的支持、组织和默许,怎能进行?因此,他是难逃法网了。明人说,刘兴祚在复州被擒欲斩,后免死。此事《满文老档》虽无直接的记载,但有两条材料可以作为参考。一是五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谕大贝勒代善:“勿绑缚抚顺额驸之子及爱塔之族人,著人看守解来,彼等之罪,尚未询明,不知本末,实属妄为。”此谕表明,大贝勒代善平定复州汉民叛逃时,曾将爱塔的族人逮捕,听候汗的裁夺。可见,刘兴祚与复州民叛之事,关系不浅。另一条材料是七月初三日的处理:“革爱塔副将之职,降为参将。”为什么爱塔要降为参将?显然是汗、贝勒怀疑他与复州民叛有关,但是,或者是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刘又善于辩解,难以定死此案;或是努尔哈赤欣赏其才,考虑其在汉官汉民心中的威望,在没有确证之前,姑且免死不杀,留观后效;还是有权贵为其求情,如像《刘爱塔小传》所说,“□□泣请,乃免”。《清史稿》卷二二八《库尔缠传》亦载称:刘兴祚因“索民财货,被计解任,遂有叛志。事屡败,太宗屡覆盖之。”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一点是明确的,刘兴祚因与复州民叛有关,被降为参将,其族人亦曾一度为此被捕。
刘兴祚的行动,很易引起汗、贝勒对汉官的猜疑。既然这个早在建州强大之前就自愿来归的刘兴祚,这个由一介布衣上升为主管辽南四卫的高级将官刘兴祚,这个曾为金国汗出生人死屡斩明兵军功累累蒙汗嘉奖的“忠臣”刘兴祚,都能改变初衷,冒着斩首籍没灭门诛族的危险,进行叛金活动,欲图归返故国,那么,那些战败而降的汉官,那些未任要职未蒙重奖的汉官,岂不是更会动摇变卦,更易与明国私通,叛金投明吗?
(四)抚顺额驸革职
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对金国汗、贝勒来说,是一个令人烦心和生气的月份,对于降金汉官来说,它更是倒霉的、令人胆战心惊、大祸临头的日子。这一个月,复州民欲叛逃明国,惨遭屠杀,早年投人建州曾为金国效尽犬马之劳的爱塔副将差一点成了刀下之鬼,就连贵为众汉官之首、身任总兵官要职、主管全辽汉民事务、荣称抚顺额驸的汗之孙女婿李永芳,也被汗爷爷大骂一顿,儿子被捕,父子险些斩首于法场。这件事情的始末暂且搁下,先讲讲李永芳何许人也,对金国的建立、巩固和扩展,有无贡献?
李永芳原是明朝游击,驻守抚顺,天命三年四月降金以后,一直竭尽全力,为汗效劳。他领兵从征沈阳、辽阳,有功,从三等副将升三等总兵官,妻为汗之孙女,尊称抚顺额驸,与西屋里额驸伶养性共同主管辽东汉人事务,名列终之前,备受汗的优遇和信任。
李永芳身受殊宠,竭力报恩,积极贯彻汗谕和八贝勒命令,为巩固金国统治做了许多事。其中,最重要的是“平叛”、“止盗”、捕逃、“防边”和被汗委以的财赋重任。金军打下辽阳之后不久,努尔哈赤就遣李永芳偕同固山额真兼督堂阿敦,带领军队,“于沿边各堡置官,教部属,置台,设哨探”。这是为了防御明兵反攻,抵挡蒙古进袭,也是为了加强控制,不许辽民外逃。天命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努尔哈赤专下汗谕,要求众汉官承担起守护边境的重任,责令他们“要与李、终二额驸商议”,对“能办诸事之好人”,对“恶逆之坏人”,不能擅自上告,必须“和二额驸共议,’,才能上报,摧升贤者。
李永芳多次遵奉汗谕,偕同女真官将,率兵镇压反金辽民。天命六年五月,因镇江民拒不降服,汗派李永芳和乌尔古岱总兵官带兵前往,胁令降顺,相机处置。李到镇江后,民仍拒降,遂纵兵屠杀,掠夺抗金人员的妻室儿女,带回辽阳,由汗分赐诸将。天命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以王备御告称托伦山村民与明总兵毛文龙遣来的蒋达、蒋萨二人密议,欲行叛逃,汗命李永芳带兵前往处理。李去后,发现村民不耕田地,变卖谷物,确将逃走,遂斩杀村民,以其子女牲畜作为俘获。
为了制止辽民外逃,惩处反金人员,全国几次大规模迁徙边境城镇和发生过抚金行动的州县居民,这件大事主要由李永芳、佟养性负责办理。天命六年十月,李、佟遵奉汗命,将多次抗金的镇江民迁往萨尔浒。第二年三月,二人又与刘兴祚,驱赶广宁、锦州、义州等河西九卫民,迁往河东,分居辽阳、沈阳等地。天命八年正月,二人又奉汗谕,前往迁移辽南沿海居住人民,逼令徙至内地。
为了控制满汉人民,防止外逃和起义,搜捕逃亡的阿哈和汉民,全国汗一再派遣官兵,清查丁口,严禁窝藏逃人。天命八年,李永芳、终养性奉命前往清查南部州县人丁,规定所有居民必须向官府如实报告本身人丁数目,告发外地逃来的汉民,若隐匿不告,“则将逃人定为逃罪,容留之人定为盗贼之罪,将此二户皆作为俘获,使为阿哈”。李永芳严厉训示所辖清查官员,责令他们“当思汗之养育之恩”,认真清查,若因收纳银物而询情不追,不查出逃人,“将上奏于汗杀之”。
李永芳还被金国汗“委以财赋重任”,收取官赋,清查余粮,运送官谷。天命七年正月金军轻取广宁后,夺取了明国存贮于右屯卫的50万石粮食,在当时年荒缺粮的形势下,这对金国汗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必需的财富,必须赶快运到辽阳、沈阳,防止明兵前来争夺,或派人烧毁。李永芳遵照汗命,抓紧办理,凑足万辆牛车,日夜兼程,费尽心机,将谷抢运回来,为缓和粮荒,增加国库收人,立了一功。
李永芳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征赋运谷,迁民查丁,平叛止逃,四处奔走,为金国的强盛和巩固尽心竭力,军功累累,政绩卓著,而且他还屡拒明廷招诱,擒谍上奏,故而屡受汗奖,赐救免死三次,可算是文武双全、效忠于汗、官运亨通的忠臣功臣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李永芳万万一也想不到,他会因出言谏阻用兵复州,而闯下大祸,险些命丧黄泉。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天命八年五月初七日,听说复州汉民要叛逃,金国汗欲发兵征讨,李永芳立即谏阻。李永芳说:“所谓复州之人欲叛者,非实也,乃系人之诬陷者。若信其言而发兵,彼方之人闻知,当乐矣”
李永芳谏阻发兵,就其言论而说,并无大错。在此前后,陆续发生过几起诬告降金汉官私通明国的案件。比如,沙场的备御王之登,因捕获毛文龙派来的奸细,于天命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升为游击,不久又升为参将,戍守炼铁的石城。石城一人伪造明国札付,捏称是乘王之登酒醉时从其置放男丁册簿的大立柜中偷出来的,向法司告发“王之登接受彼方尼堪之札付”。法司审理后断定,此系诬告一,特专门送信给王之登,告诉他说:“此首告者是诬告,尔勿担心,好好管辖地方。”努尔哈赤自己也说过:辽东巡抚和道员等官,常遣人送信来,“种种诬谤抚顺额驸、西屋里额驸”,并诬陷汗所任用的八游击等官,“以激我怒”,斩杀降金汉官,“然我等不中其计矣”。让八游击“详查其诬陷之人”。
李永芳的谏言,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陈述的。他主张慎重,不要轻易发兵,以免误杀,这将招致明国官将嘲笑。而且,估计他还有一段话没有说出来,或者是《满文老档》没有载录。这就是,轻易发兵,不分青红皂白地滥肆杀掠,必将激化已经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将遭到辽东汉民的坚决反抗,那时,举国叛逃,就不可收拾了。缓发兵,慎杀掠,先调查,后动手,这就是李永芳谏阻的理由和建议。
李永芳之所以站出来阻止立即用兵,可能是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种可能是,他忠于金国汗,害怕铸成大错,冤杀滥杀,丧尽民心,会招致辽民更加拼死反抗,对金国统治不利。第二种可能是,在此之前,李永芳在辽南州县呆了几个月,专管查丁、平叛、止逃,对这样全城合谋叛逃之事,却一无所知,刚回都城,就有复州人来密告,岂不是玩忽职守,怎能逃避知情不报心向明国的嫌疑,征讨以后,自己就将蒙受通叛之冤,轻则贬官降职,重则袅首示众满门抄斩,倒不如以攻为守,阻止发兵,搁平此事。第三种可能是,李永芳知道复州将叛的内情,或者自己的儿孙族人亲友与此有关联,想借此谏阻,保护他们免遭屠杀,并在叛逃归明以后,让明国为己记上一功。根据李永芳以后的行动来看,显然李永芳及其儿孙并未参加这一叛逃案件,而是一直尽忠于金,死不回头。连清朝政府官修的《国史列传》,也载称李永芳“归诚最先”,“明巡抚王化贞及边将,屡遣谍来诱,永芳执其人并书以闻,上嘉奖,赐救免死三次”。
姑且不谈李永芳谏阻的内心动机,而就事论事。不管李永芳是怎么想的,就其谏阻本身而论,他的谏阻,理由充分,建议正确。在辽民猛烈反金的浪潮冲击下,先调查,后用兵,防止冤杀无辜,避免事态扩大,这个建议是妥当的,这个谏阻是合理的,不应加以非议。
但是,被辽民反金斗争气昏了头的努尔哈赤,虽然素以聪睿自诩,此时却不英明了。听到谏言之后,他竟对一向忠心耿耿为金国效劳的抚顺额驸大发雷霆,严厉训责,痛斥李永芳忘恩负义,不识天命。他下达长谕,历数李永芳的过失:
汗怒其言,下书于抚顺额驸曰:李永芳,当初于抚顺获尔之时,念尔系一知觉明白醒悟之人,故携尔而行,以我金之骨肉给与尔矣。蒙天眷佑,征讨叶赫、哈达、乌拉、明国之四路,以及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东、广宁、蒙古边塞等处,此等地方上天眷爱而给与我,尔李永芳却不相信。因尔之不信,故尔等以为明帝久长,而以我则为短暂矣。辽东汉人屡欲谋叛,彼方之人密谋之书不断而来,吾常令清查而收捕之,因尔心向明国,竟以欺瞒而谏阻于我。叛逃彼方,尔心中以为善,发觉而杀之,则尔心不适矣。尔若果真正直,不苦累兵士,不劳累国人,尔身承受而管辖,叛逃皆止,平定国人,灭其国而携来,则系我之过,尔之谏宜也。尔贱视于我。我闻之,尔之汉国刘邦,曾为领催淮下差役之亭长,蒙天之枯而为汉帝。赵太祖乃街上之无赖,亦为天枯而为帝,且传数世。朱元璋,身无父母,独行乞讨,曾为郭元帅之下役使,并为天所枯而为帝,传十三四世矣。
尔若欲通明,北京城之内河,两次流血矣。各衙门大树之根,被风拔之矣。上天所显示如此异兆,岂尔之谏阻能止之乎?可见尔将辜负育养之父、岳父矣。以尔为婿而养之,蒙古、明国、朝鲜皆闻之矣。若治罪,他国之人闻知,亦将嘲笑于我,也将嘲笑于尔,念及此,故不罪尔,默然处之,然我心怨恨,乃示此由衷之言也。
努尔哈赤实在是气昏了,糊涂了,分不清真假虚实,硬给李永芳扣上“心向明国”的帽子,而且还不顾自己赐与李永芳免死三次的救书以及宣布“不罪尔”的汗谕,对李进行了惩治,李永芳的几个儿子都被拘押捆绑。直到五月二十三日,他才下达汗谕,告诉大贝勒代善,“不要捆绑抚顺额驸之诸子,及爱塔之族人,派人看守送来。彼等之罪,尚未询明,不知本末,(那样做)实属妄为”。五月初九日,大贝勒代善领兵前往复州,屠杀反金人员,六月二十八日回辽阳。七月初四日,革李永芳总兵官之职,初七日又复其职,李永芳又当上了总兵官。但从此以后,努尔哈赤及诸贝勒对李永芳就不太放心了,不如过去那样重用和信赖,总管汉民事务的重任,落在西屋里额驸、总兵佟养性身上了。
努尔哈赤这次对李永芳的斥责和惩治,是严重的失策,犯了一个大错误。从李永芳的过去、现在和以后的行动看,他是始终效忠于金国汗的。他的儿子李率泰、巴颜等人,也任至固山额真、尚书、总督,巴颜还因袭父爵职和立功,由子爵(总兵官即后来的子爵)晋至一等伯。李永芳是八旗汉军官将中之元勋和功臣,其家乃汉军中的名门大家。努尔哈赤把这样一位归顺之后永远效忠的功臣之谏阻,斥之为“心向明国”,是“欲助”明国,这个结论完全是无中生有,信口开河,没有事实根据。这是一个冤案、错案,影响很坏。像李永芳这样“归诚最先”,背叛故主明帝,效忠新君金国汗,为巩固、扩大金国统治而出生人死,四处奔走,效尽犬马之劳,这样可靠的降金汉官,都因忠言直谏而遭到英明汗的严厉斥责,并且不念其前劳,不思其旧功,严加惩治,甚至差点问斩,那么,其他汉官怎么办呢?他们归顺在后,没有那样多军功,没有那样多的劳苦,也不像李永芳那样受到汗的重用和信赖,又不是汗的孙女婿,既然李永芳都会因直谏而被怀疑为“心向明国”,罢职问罪,蒙受冤曲,他们这批汉官就更可能被突然治罪斩首抄家了。金国汗这样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实在叫降金汉官寒心。许多汉官更加动摇了,对金国汗的忠诚亦大大减少了。
总之,天命八年三月努尔哈赤指责众汉官不忠,五月训斥李永芳,捆绑其诸子和爱塔的族人,七月初四日革李永芳总兵官,爱塔由副将降为游击,标志着金国汗对待汉官政策的大变化,从过去的大量任用汉官、依靠汉官,转变为怀疑汉官,歧视汉官,疏远汉官。努尔哈赤的这个转变,是十分错误的,它使真诚降金的汉官心灰意冷,无所适从,使那些原本观望三心二意的汉官更加犹豫,更加动摇,扩大了汗、贝勒与汉官之间的裂痕,双方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这样一来,也使汉官更为胆小怕事,三缄其口,三思而行,不敢各抒己见,陈述军国大事,更不敢犯颜直谏,阻止汗、贝勒滥施杀掠,革除害民弊政。努尔哈赤空前孤立了,听不到汉官的忠言,不知道怎样处理军国要务,尤其是在对待汉民的问题上,更是闭目塞听,一意孤行,迷信武力,大肆杀掠,把整个辖区搞得百业萧条,田园荒芜,天怒人怨,民不聊生,金国的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
|
|